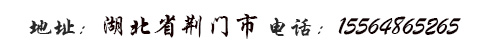贸院的那些人和事
|
揪出孩子暴躁的真正因素 http://www.zgbdf.net/baidianfengjiankangzixun/xiyizixun/m/53054.html 贸院的宿舍楼旁有一片湖,温碧如玉,沉和静美,晴朗的日子里,倒映着辽阔的天空和舒卷的白云,别有一番韵致。而我们91级的同学们就象春天里岸边丛生的芦苇,单拎个的拿出来,朴素平凡,从不竞秀争锋,然而细观之又各有特色。更可贵的是,和风畅雨下,紧密团结,互相衬托,远看处,便是一片郁郁葱葱,生机盎然。四年的时光,为仙的成仙,为神的成神,称姐的做姐,装哥的做哥,而又不失人间烟火味,满满的记忆堆砌成青春。几十年过后再回首,竟感慨万千,想说的太多,却又不知从何说起。 就先从所谓的“神”说起吧。 91级经济系毕业合影 诗人 上学期间,一本黑色封面的《五人诗选》在同学间传阅,甚为流行。其中摘录的都是著名的朦胧派诗人的作品,如北岛,顾城等。于是,当某某牙齿比嘴唇跑得快(俗称“呲牙”)的老师乜斜着眼镜“......"(此处省略ABB三字)地盯着我们那些漂亮的“姐”的时候,或者平时正气凌然不容俗恶的同学私下去六楼找系里老师汇报思想的时候,便有某君在人群背后正声朗诵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其实,此君也算不上真正的诗人,顶多是雄性荷尔蒙沸腾的“文学青年”。真正的诗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哪怕人生不惨淡,他也要直面设定的惨淡,就象堂吉诃德举起长矛冲向风车一般。水木就是真正的诗人。基于此,紧锁双眉,倒背着双手,当然手里要握着一本书,倒贴在腰部略微靠上的位置,踱着沉重的步伐,不时长叹一口大气,这便成了他在四年的大学里留给我的标杆式的形象。这样的形象如同烙在我的记忆里一样,至今鲜明如昨日。 诗人傲然处世,濯然自珍,轻易不与人语,能聊得上来的零落如尘。我有幸是那几粒尘埃之一。诗人偶尔在大课之后送我一页新作,索要读后感。说实话,我对当代诗颇为头疼,读起来如同求解倪几何老师教的微积分一般,找不出头绪。这满纸的八竿子打不着的词汇排列在一起,哪里的逻辑,哪里的语法,哪里的干活(日本话都憋出来了)............咦,好不容易找到一句通顺的现代汉语,还断成了好几行,读得让人呼吸不畅。但我明白,这一定是诗人的呕心之作。每个词汇背后都站着一个紧锁双眉的影子,那一声一声泣血的杜鹃;每一行排列都意味着教室外楼道里来来回回无数次沉重的踱步,那一刀一刀的搜肠刮肚。于是,我往往很郑重地接过来,认真地阅读上N遍,努力地理解着诗人深邃的思想或者痛苦的领悟。然后我会一本正经地,有时也不知所云地讲出自己的想法。诗人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摩挲着下颌,无言地倾听,不时地点头。临了,伸出右手(一定是右手),重重地拍一下我的肩膀,转身而去。在他身后,是万千拥趸追随的空气分子。此刻,我也会如释重负,再赴我俗世生活。 后来,这样频繁的高端峰会越来越成为了我的压力。我感觉已经不能仰瞻他的高大形象,而在那些光辉的作品里,即便我在汉字的缝隙里钻进去跑出来,又钻进去又跑出来,累得气喘吁吁,还是找不到我能理解的逻辑。于是,我经常躲着诗人走。在猫捉耗子的游戏里,我竟稀里糊涂地成了可怜的老鼠。但老鼠也有老鼠的快乐,痛并快乐着。。。 时光飞逝如电,转眼到了临近毕业的夏天。一日,宿舍的几个兄弟在食堂前面的夜摊上煮了飞鸡蛋的方便面,各自端着热气腾腾的饭盆往宿舍楼奔,要赶场暂时休战的大富豪游戏。记得那时的饭盆是尿盔式的,现在想起来很滑稽。大家脚步匆匆,刚走到自行车棚旁,突然黑洞洞的车棚内窜出一道身影,径直挡在我的面前。我的妈呀,上帝安拉弥陀佛呀,吓得我灵魂差点狠狠地吻了大地。定睛一看,原来是诗人。 诗人依然是一脸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的凝重,低声道,“我想和你谈谈诗”。 旁边的哥们朝我挤了挤眼,一个诡笑,直条条地弃我而去。 我无奈地对诗人说:“我已经很久不写诗了”。 “那咱谈谈文学。听说你最近写文章如腹泻,说来就来。”诗人道。 “道听途说,我便秘好些日子了!”说完,我落荒而逃。 毕业后,诗人回了家乡,如夜行的孤雁,失去了联系。后来出差去过几次他的城市。可是,他就象落在那个城市里的雨滴,明明知道在那里,却怎么也找不到。随着年龄的增长,愈发地怀念曾经谈诗的日子,愈发地想念诗人。 生活的苟且,让我们忘记了诗和青春,但诗人的形象,成了我贸院生活中不可磨灭的印记。 仙哥 刚上大一,班里组织活动让大家彼此熟悉。 打扑克是一种简单易行且收获颇丰的项目。偶尔的一次打扑克之后,我提议用扑克给大家算卦。出于起哄成分居多,大家拍手应之。忘记了第一次是给谁算的了。我用六张扑克作六爻起卦,结合高中自学过的易经知识,问事答疑。初战竟大获认可,该同学连呼灵验。后来,又占数次,都说“太准了”。站在风口,成名就是这么容易,“仙哥”之名迅速扩散,传遍整个九一级。外系的女生纷至沓来,教室里排队等着算命 现在想来,纯粹是文学加持了我,感谢文学,前后十八世地感谢文学。说的是一些概念模糊可左可右的卦辞,剩下的就是问卦人自己想象力的发挥了,怎么想怎么对得上。再加之宿舍哥们们的广告渲染,“仙哥”之名竟然坐实江湖,本名险被遗忘。 狐仙 班里有个北京姑娘,个子瘦小,却极善短跑,贸院田径队里百米的一员悍将。她和DOCTOR同桌,DOCTOR是逄承国老师给起的外号,因为哥们的英语超赞,闲得无聊时背朗文词典玩,后来果然去美国读了博士,世间朗朗,却也有冥冥中的注定。DOCTOR很老实,经常因为上课时越过北京姑娘在课桌上划的界线被掐胳膊。DOCTOR小心再小心,怎奈界线被北京姑娘不断涂改,生存空间越来越小,总免不了被掐的结局。回到宿舍,男生们经常凑热闹去看DOCTOR胳膊上有几处红色印痕,这成了我们中的热点话题。于是,有好事的大侠给北京姑娘起了江湖绰号“狐仙”,绰号由本名谐音而来。 但狐仙确实刁贫善辩,得理不饶人,霸气得很。这是当初的印象,前些年,在墨尔本遇到她,仙姐已经变身为健身达人外加墨村菜农。自己后院种着各种的蔬菜,养着几只蛋鸡。鸡粪作肥,菜叶喂鸡,小生态纯有机。自给之余,经常将新鲜的蔬菜和土鸡蛋送给邻居和朋友。我刚到异国他乡,一切摸不着门道。是她开着车带着我们全家到处跑,豪爽侠义,让我体会到一股浓浓的亲情。 二仙门 班里组织活动,但男生和女生两个阵营意见不同,针尖麦芒,互不相让。几次商讨未果后,男生推举出仙哥,女生指定狐仙,让我们二人单独约会谈判,时称“二仙门”。具体地点和过程已经消散在记忆的迷雾里了,总之这场重大的外交事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以谈判破裂告终。之后,我们班陷入了相当长时间的男女冷战中。外班男生也抓住了这千载难逢、念了几世佛转了几座山修来的机会,乘虚而入发展自己的势力。等我们男生幡然醒悟的时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领地里的女神们牵着外班男生的手走在了去往食堂的砖石路上。 “二仙门”事件后不久,我们班男生以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手法从生活委员(女)那里骗出了班费,甩掉了女生,购买了一整套水枪装备,大闹水上公园,也开启了贸院男生宿舍楼的战争篇。这是另一个章节,以后另述。 华仔 九一新生晚会上,有一个小虎队的节目,三只虎来自国贸系的两位和外语系的一位男生。装束是当时风靡的风衣加烫吹发型,以载歌载舞的形式轰动全场,一炮走红。九一“哥时代”拉开帷幕。贸院穿风衣的男生瞬间多了起来,而且凡穿风衣的男生往往能很快地牵手女生,共同迈入食堂或图书馆。在贸院,一起去食堂打饭吃饭,一起去图书馆占座,是正式搞对象的标志,是向孤独的奔跑者的强有力的无情的宣战。 按下外语虎哥不表。他的宿舍里还有一位男生,来自大连,平时缄默少言,不占风采。亦是偶然,试了一次风衣装束。有人戏语,你象刘德华耶。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于是,在后来的四年里,该哥成了贸院的一道风景:一袭黑色的风衣,风吹不倒的摩丝发型,黑得看不到后面的太阳镜,永远的挺胸抬头冲向火线的行姿,风雨无阻,四季如歌。 晚自习后,食堂的大师傅们会在外面的空地上摆起地摊,一排砂锅在跳跃的炉火上吱吱歪歪地哼叫着。或煮方便面,或煮云吞,奢侈的搭配是飞鸡蛋或者加排骨。加夜宵的同学蜂拥而至。 贸院的规矩不是人排队,而是用饭盒排队。交完钱,把饭盒放在桌子上排个儿。等着的同时,大家说说笑笑,三五成群,男女相杂。偶然间,若大连哥出现,男生们会调侃道“刘德华来了!华仔!”当此时,大连哥会先把饭盆排在队伍后面,然后很自然地将身儿挪至在砂锅架前,孑孓独立,用风衣、墨镜和风吹不倒的发型定格成华仔的形象,巍然不动,任尔东南西北风,当然也有炉子里飞出来的煤灰。自信爆棚!华仔,我们爱你! 今年,在六纬路的饭馆里和华仔聚过一次。啤酒烤串,花毛一体,聊的尽是孩子上学的事。哥们已经不再穿风衣,有些发福,但头发依然很好。上听(四声,喝多了的意思)之后,说起过去的事,大家摇头苦笑。岁月无刀,但生活会把哥改造成大爷(大叔的意思)。 说句天津话,我们都成大爷啦。。。 (待续) 朱栋华于年5月19日深夜 本文作者 附:朱栋华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贸院我的站牌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jz/8596.html
- 上一篇文章: 八面山的黄根柴中篇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