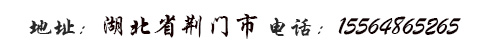八面山的黄根柴中篇
|
八面山的黄根柴 (中篇) 学校停课以后,在父母的百般催促之下,我很不情愿地踏上了外出学艺谋生的道路。此时,我的全部心愿都在升学考试上。在外出学艺的出发前,我反反复复地要求父母答应,一得到升学考试的消息,要马上通知我,我要马上回来。直到父母肯定地答应了我的要求之后,我才带上简单的行装,并带上初中的课本,离开了从小生长的故土,来到了陌生的异乡。 这里是浙赣线上的一个小站,叫浦阳站,我们的工地就在就这小站附近的一个采石场上。这是一个很大的采石场,整天轧石机轰鸣,大量生产着铁道上用的道渣。 在浦阳站附近还有一个小村子,叫谢家。由于供工人居住的工棚还没搭建好,我们这些人就暂时分散住在这个小村子的农民家中。 我们借住的房子在这个村里讲来是全村最好的房子,房子里还装饰着天花板,这在当时是很少见到的。听房东说,邓小平几年前有事耽搁,火车在浦阳站停留,那时就住在这房子里。当时我就想,邓小平这么大的官住在这么普通的地方,当时肯定是在落难中。 白天,我在工地拌水泥浆,担石头——刚学艺的学徒开始时往往都是干这些活。因为离开铁路很近,在工作的间隙可以看看火车。巨大的蒸气机车牵引着一列列满载的货车和一列列蓝色的客车在铁道线上南来北往地飞驰。时而,一列满载大炮、坦克的军车在急急地向南方赶去,想必当时东南沿海局势有些紧张。 晚上,我在宿舍的灯光下看书,复习功课。工友们很诧异这个小学徒竞带着这么多的书来学手艺。真想不到不久前还是读书的学生,转眼就成了做工的学徒。 不过,我的内心深处是没从这个角色转换的过程中恢复过来。我总是认为,自己是个读书的学生,来这里做工是暂时的。也许明天,或许后天,家里就会来信,我就要回去读书的。 秋天到了,成群的大雁正在向南飞。它们随着空中气流的方向,一会儿排成人字形,一会儿排成一字形。它们这样做是为了节省体力。它们日夜兼程,急急地往南赶路。那里是它们越冬的栖息地,是温暖的地方。 寒风刮起来了,冬天到了,最后一群大雁也飞走了。我呆呆地仰望着空荡荡的天空,心中渐渐涌起阵阵不安。家中这么久也没有来信,父母亲看来要食言了。 寒风吹袭着,砂浆腐蚀着,刚到冬天,我的双手就肿得很大。在劳动中,坚硬的石块瞌碰着手,不久双手就伤痕累累,冻疮串串了。两只手的手背上布满了流着血水的疮口,劳动手套戴在肿胀的手上被绷得紧紧的,劳动时受到震动,不时地把疮口迸出一阵阵血水,把一双手套染成怪怪的红色。中午吃饭时是带着手套吃的,因为手套被血水沾住脱不下来。傍晚收工吃晚饭时,总得把手套除下来。先到锅炉房打一盆热水,把戴着手套的手在水中浸透,然后才好脱手套。想请工友帮忙,工友看见这血淋淋的样子受不了,不肯来。没有办法只好自己动手。尽量不去看手,几乎是闭着眼睛,一点点把手套撕下来。等除下手套,不知是痛还是紧张的,浑身都要出一身汗。等除下手套,才长长出了一口气。洗净手套,挂到锅炉房烘干,准备第二天用,把变得红红的一盆水倒掉,这才算是完成了吃晚饭前的一项必须要做的工作。这是那时我每天精神压力极大,最不愿做但也不得不做的一件工作。 工棚搭建好了,工友们都移住到工棚了。冬天的寒风不客气地从简陋的工棚的缝隙中钻进来,在整个工棚里肆无忌弹地游荡着,工棚里是很冷的。 两只手象被什么东西在啃咬一样一阵阵地痛,这又痒又痛十分难熬,正在看书的我不得不放下正在看的书。我无望地看着眼前翻开的书本,脑子里是一片茫然。离家数月了,看来父母是不肯让我回去读书了。此时同学们一定已经坐在温暖的教室里读书了,而自己却在这异乡的土地上受这寒冷和伤痛的折磨。我感到自己象是一只被遗弃的小雁孤独地在寒冷的夜空中飞着。它一边可怜地哀叫着,一边跌跌撞撞地向南飞,向同伴们飞去的方向拼命地飞。 鸿雁北归还带上我的思念 鸿雁向苍天天空有多遥远 ▼ 心中的苦痛,肉体的疼痛一齐向我袭来。一股从心底涌出的委屈使我的眼泪不可抑制地涌了出来,一滴一滴地落在翻开的书页上…… 春节将近,工地散伙了。归心似箭的我一到家里就急不可待地去了解学校的情况,在得知学校还没进行过升学考试,同学们还都在家待学的时候,一颗焦燥的心才放了下来。细心的母亲很快就发现我手上的累累伤疤,她惊问其故,我说了原委后,母亲落泪了。自此以后,容易引起母亲落泪的事我都避免在母亲面前提起。 从此,等待考试的期盼一直顽固地驻扎在我的心底不肯离开。后来逐渐演变为一个要经常出现的梦境了。在梦境中都会有有关考试的情节,或是一道题还没理解在手忙脚乱地翻书找参考资料,或是一本课本不见了在翻箱倒柜地找,或是同学们都坐在考场里了我还在路上拼命地向考场跑。等到惊醒时,全身都是浑身大汗。 这样的梦境,这些年一直都在延续,不过内容已由中考变为高考了。对这经常做梦的事,有人说要去请医生看看,医生说要治疗。我不想去请医生看,也不想去治疗,我还是想让这充满期望的梦一直做下去。人生本来就应有想头,有期盼,有期盼总比没有期盼好,哪怕是在梦中。 在那火红的如火如荼的年代,狠抓阶级斗争是一种时尚的举动。各种形形式式的“运动”后期,“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全体家庭成员惶惶不可终日的窘状,始终是运动的一种重要的副产品。 这次“运动”后,所有的谋生之路都被封堵了。不能出门学手艺,不能搞副业,唯一能让你可以谋生的是种田。 我定下心来开始扎扎实实地干农活。我在心里告诉自己,因为自己天生条件不好,要准备比别人吃更多的苦,受更多的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上有一个立脚之地。 冬天,凡是出工劳动的时候,我都是赤脚穿着“皮草鞋”(注:用废旧手推车外胎和铁丝自制的鞋,可代替草鞋)。赤脚草鞋踩在如雪的严霜上,踏在如刀的寒冰上,刺骨的寒冷直透心底。但我却一直告戒自己:“熬住!熬住!干活干了一会儿就不会冷的,寒冷的痛楚就会消失的。”在那改田改地的整个冬天,我都是这么干的。我以自己皮肉受苦的代价,节省了几双宝贵的尼龙袜。 难忍的还是夏天。火辣辣的太阳,炎热的天气,长时间在阳光下从事高强度的劳作,使我虚弱的身体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在繁重的劳作中,在闷热的空气中,我象一条在缺氧的水中的鱼儿一样,张着嘴大口大口地吸气,热得人几近昏过去。 一团热气又围了过来,热气中裹着的黄根柴的辛辣气味使我的本来就艰难的呼吸几近窒息。在神志有点恍惚中,我拿出曹植先生的七步诗篇,对黄根柴的助纣为虐,落井下石的不义行为进了抨击。“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注:作者在神志恍惚中产生的幻觉和切实的思想感受。) 用手推车拉石头是一种很需要体力的活,尤其是在夏天。老拉车的人说:“拉这种车要有“弹力”。所谓”弹力“就是长期磨练而成的好体力,持久的耐力和熟炼的技巧。我刚学干活,当然不具备“弹力”,但为了多挣工分,我也拉起了石头。 我往手推车上装上了近千斤的石块,顶着焦灼的太阳向目的地行进。一会,汗水就湿透了全身。初一看,别人还以为你刚从水里爬上来。 前边是一段长长的上坡路,上坡路是拉车人最艰难的路。在上坡路上拉车,不进则退,但退是不好退的,因为独轮手推车一退很容易失去控制,一失控,马上会车倒石翻,弄不好,也会连人带车摔下高高的堤坝,后果不堪设想。我也明白上坡拉车不进则退的道理,无奈力气不济。我紧握车把用尽了全身的力气,脚筋都蹬直了。我看不到自己的脸色,也许是涨得紫红,也许是憋得煞白,只觉得一颗心在急急地狂跳,喉咙里咸丝丝的,一腔鲜血马上象要喷出了。突然一只手,有力地拉了一把,把我拉离了摔下深沟的境地,是同伴助了我。 艰难的生涯大大增加了遇险的概率。在高高的脚手架上,在险峻崎岖的山道上,在接近人的生理极限的劳作中,我经历并逃过了许多次危险,这许多次危险每次都可以是我的灭顶之灾。 年开始修建的南江水库,它所使用的民工完全是由地方上无偿提供的。当时我也被派去参加水库建设。 在水库工地,每个公社的民工组成一个连,连里接受一定的任务分给排、班。分到的任务一定要完成,而且在实施的时候,连里还要求超额、超时完成,这就给本来就很重的任务增加了完成的难度。当时,在民工队伍中,我是年纪最小的民工之一,体力技能都不及他人。为了不影响大家任务的完成,我总是拼命地干。 水库工地上,大坝两头的山上架起了1万瓦的长弧氙灯,把整个坝区照得如同白昼。 这晚是湖溪连队的夜班,任务是给拌搅机加料。南江水库工程的建设,是典型的人机混合施工。虽然在施工中使用了许多机械,但是在采集沙石料、运沙料、运石料,给拌搅机进料等体力活,都是靠人工手抬、肩扛来完成的。所以南江水库民工的劳动强度是很大的。我亲眼见到好些人在工地干了一天或几天就吃不消跑了。 今晚我们将在雨中用原始的肩扛手抬的方式来喂饱现代化机器的钢铁之腹。机器启动了,民工们每两人抬起—斤的砂石料开始跑,向设在高坡的拦搅机房跑。一定是要跑的,否刚是供不上机器的需要的。 一长溜拌搅机架设在高坡上,一大波人潮扛着大筐涌向高坡,一大波人潮抬着空筐退下高坡,回到料场,重新装料,接着另一波人潮又涌上高坡。机器在轰鸣,人潮在涌动,人和机械组合成了一台巨大机器,在风雨中急急运转。 衣服湿淋淋了,不知是汗湿还是雨淋。步子迟纯了,不知是乏力还是肚肌。看那机器,没有汗流,也不知肚肌,仍是精神饱满,毫无倦意! 确实是肚肌了。在这高强度的劳动中,每日的饮食是不足以支付如此之大的体力支出的。凌晨1点,是工地吃夜餐的时候了。今晚的夜餐是在深秋的雨中吃的。天上落下的雨,笠帽上流下的雨,一同混在饭里、菜里,成为民工们再次抬筐的燃料。 天快亮了,雨也下得小了些。由于体力的透支,热量的丧失,湿淋淋的衣服穿在身上使人很冷。我步履沉重地重复着这繁重的劳动。人是非常地疲倦了,疲倦得脑子都麻木了,什么事都懒得去想,只能机械地一步一步走着……走着…… 涌动的人潮渐渐乏力了,迟缓了,而机器仍在精神抖擞地飞转着。开机器的工程队的工人们目睹民工们的劳累,也动了恻隐之心。他们没等领导的同意便自作主张地调慢了机器的运转速度,使极度疲劳的农民兄弟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 秋天的雨夜,紧张的水库工地,这在从事新闻报道的记者们眼中是一个多么好的素材!他们可以把它写成诗情画意的夜晚,写成浪漫的故事,也可写成慷慨激越的赞歌。可是我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我只能写出劳动者的辛苦,劳动者的感受。我身临其境地参与了劳动者们的劳动,我懂得他们的想法,懂得他们的感受。旁观者和参与者是不一样的,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他们的感受不一样,他们的观点也会不一样。因此,这个原本可以是诗情画意的秋夜,留在我的记忆里的是劳累、饥饿和寒冷。 想必是老天认为给我吃的苦还不够,他又给我安排了一个人生的磨难。那一年我全身各处莫名其妙地出现了一些白色的斑块,不痛也不痒,经医生诊定,说这就是白殿风。 听医生介绍,白殿风是一种顽固的皮肤病,目前还没有有效的办法能够治好。金希聪老中医还列举了一些具体例子,说某人患白殿风,医院没医好;医院去医过,也没有办法治好。但不管怎样,有病总得想办法治,但治病是需要钱的。 为了治病,我不管会不会被扣上投机倒把、长途贩运等帽子,决定去担柴卖,以此来赚一点钱。因为在生产队里劳动一天也不过几毛钱。 我跟着几个老担柴的乡民起了个大早,在凌晨2点钟左右就出发了。走了大概十里路,在西堆村附近的沿山路上,我看见了东方的天空中悬着一个奇怪的星星,一个很大很明亮拖着尾巴的星星,很象一把扫帚。在书上我看到过这种星星,知道它叫慧星,俗称扫帚星。 在民间传说里,扫帚星是一个不吉祥的东西,也不知道是不是真有这种事。我把扫帚星指给大家看。大家一边赶路,一边看,倒也增加了一些乐趣。 常去担柴的同乡告诉我,因为柴稀缺,今天担柴要到横山去担。从家到横山有将近50里。一路向东行,经过西堆村、岭脚村,接着要翻过十里路的梓誉岭,到达梓誉村,再翻越十里路的葛坑岭后,走一段山路就到横山。这里已是深入到盘安县境了。 听说要走这么远的话,我心里有些发怵,但也只能硬着头皮走下去了。一路上倒也山青水秀,风景很美,但心里有一个担柴的负担也没什么心情看沿路的风景。倒是肚子饿了,提前把当午饭的玉米饼吃了一些。这也不是我贪吃,是因为那时每天吃得差,肚子里底子空,人就会特别感到饿,就特别想吃。 在横山村村口,我们碰到了一群当地妇女。这些妇女自恃有柴可卖,高人一等,把我们这些担柴的“外洋人”很是轻视。她们趾高气扬地向我们告知,村里有规定,不准进村买柴!甚至最后通谍一样地声称,要去找来她们的最高行政长官——生产队长!她们反反复复地提起小队长,其神情,其语气是那样自豪和虔诚。我不禁有些惊讶,想不到在这偏远的小山村,权力的统治竞也这么厉害! 我们大家陪着小心,生怕惹恼了这些妇女后买不到柴,这样一天路就白走了。我们当中一些年纪较大些,社会经验丰富些的人则与她们虚与委蛇地周旋。说她们的好话,戴她们的高帽,不失时机地称赞她们,赞美他们,把这班妇女哄得眉开眼笑起来。她们这才允许我们进村去买柴。 经过这一阵耽搁,等到大家都买好了柴的时候,已快到吃中饭的时候了。想到回程是这么远,同行的一位年青的姑娘竞哭了起来。 回程确实是艰难的。挑着沉重的柴担,一步一步翻过两座高岭,几十里山路。有限的食物早已填不饱饥饿的肚子了,那就喝山水来充饥来解渴吧。 这是梓誉岭上坡度最陡的一段路。肚子空了,脚哆嗦了,柴担显得更重了。我放下搭柱(注:挑担时用的辅助工具),拄在地上,挑着柴担一小步一小步地向岭上挪去。 太阳已经西斜,看来回到家里是要到晚上了,生活是如此的艰难,赚钱是如此的不易,还有那个令人心堵的白殿风顽症!我心里怨愤难平。谁主宰着我的命运?谁指使苦难如影相随地紧紧跟着我?谁以苦难对我的人生苦苦相逼?! 一股黄根柴的气味随风吹了过来,剌激了我激愤的神经。我把一腔怨气泼向了黄根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相煎何太急!”我忿忿地念叨着,挑着这斤柴担上了山岭。 高昂的医院望而却步,而医治白殿风等顽症所需的医疗费,更不是当时的我所能承受得起的。唯一的办法,只有找土方、特方试试,来试试自己的运气,来搏一搏自己的命运。 在浩翰的书海中,一段文字使我的眼睛一亮。在《科学实验》这本科普刊物中,我看到了期望已久的资料——制斑素,用于医治白殿风。用法:肌肉注射,涂抹患处后,晒太阳15分钟。希望之星亮了! 我在当地药店很顺利地买到了这种药。这是一种很普通的药,为针剂,是深褐色的液体,很便宜,是哈尔滨某药厂生产的。医院,问了医生,医生说不知道这个药,医院里也没有这个药。他们也不肯给我注射,怕承担责任。后来,我去了村医疗室,那里有熟识的金希聪老医生。讲好了以后,由赤脚医生按我自己说的用量、用法为我注射。当然,后果得我自己负责。于是,由我自己当病人又当医生的治疗,就这样凶吉未卜地开始了。 我每天午饭后去医疗室打针,然后跑到太阳底下去晒。七月骄阳如火,晒得我涂了药液的皮肤起泡、流水。半个月过去了,医疗效果还没看到,头、脸却都肿了,心里的压力确实一天比一天大了。 白殿风,这个难治的皮肤病。不会传染,不痛不痒,对健康也没多大危害,但它巨大的杀伤力在于对患者的精神有巨大的伤害,这对于当时的我尤其如此。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本来就处于劣势的我可就经不起这个伤害了。婚姻还没落实,事业还未成就,如果白殿风医不好,婚姻、事业都将远离我而去了,如果是这样,活在这个世上是生不如死的。 头脸一天比一天更肿了,肿得看看不象人的样子了。家人们、朋友们怕我出危险,劝我停止打针,停止治疗。我惨然一笑,不予置理。希望象是在一天天在破灭,我的心逐渐变为一潭死水。这是心灵绝望的可怕的死水。任何风暴怕也激不起这潭水的一点波浪,就算是生命的危险恐怕也荡不起这潭水中的一圈涟漪。 风萧萧兮荆溪(注:南江中段的俗称)寒,壮士一去兮何能还!这首我嫁接过的古歌词,也许就反映出当时我心里的绝望和无奈。只是在最后三个字“何能还”上还保存了一点渺茫的希望。 27岁,是生命之花开得最灿烂的时候,而我当时的解读是离开这个世界的合适时候。没有妻子儿女的拖累,父母也有兄弟们能瞻养,没有我不会对现有的一切产生影响。我也珍视生命,但我不留恋生命,如果是没有质量的生命,我宁可选择后者。我一生平凡普通,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唯一值得我深深留恋的是亲爱的母校,三年来朝夕相处的亲爱的同学们。如果我真的离开了,我只有在另一个世界为他们祝福了。我不会主动地终结生命,当一切希望都破灭的时候,我倒希望有一个外力把我的生命带走。 一边是躯体处在炎热的骄阳之下,另一边是心灵处于冰冷的冰河之中。我在冰与火的煎熬之中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夏天。 金色的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那个季节,作为对农人们辛劳的酬报,大地都会向他们赠送礼物,这礼物就是丰硕的果实。 或许是青春感动了上帝,或许是知识拯救了生命,在那个金色的秋天里,我也收获了一颗丰硕的果实,那就是身体的康复。 生命的阳光重新照进了我心灵的深处,心灵的生命之花重新绽放了!心也轻松了,身也轻松了,整个人的感受象是涅槃再生了。 当我高高兴兴地走进村医疗室的时候,阅历丰富的金希聪老医生怔怔地看着我,好长时间都不相信这是真的。 在以后的年月中,不时有一些白殿风患者找上门来,向我讨教治疗的办法,我当然毫无保留地告诉他们。遗憾的是有些患者告诉我,制班素在市场上不见了,这种极普通的药只在网络上留下了它的大名,只看到了许多焦急的患者在网上求购它的留言。 我也感到深深的的遗憾。遗憾自己当年治好了病之后没有把它大力推广,遗憾自己当年不主动一些去扩大它的影响。如果是那样的话,这种可为千千万万患者造福的好药也许不会消亡。看着患者们求药的急切的眼光,我的心里渐渐地由遗憾变为内疚变为自责了(未完待续)。 ——璀璨之星倾情奉献 像星星一样 在夜空中闪耀 璀璨自己 也有余光照亮别人 ▼ ◆◆◆因为欣赏所以分享◆◆◆ 欢迎分享给朋友圈,记得给璀璨之星点赞。 公号转载须经授权,不得用于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jz/8593.html
- 上一篇文章: 比宜家好看还便宜的百元小物链接都给你
- 下一篇文章: 贸院的那些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