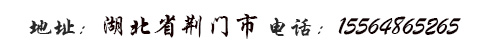一本关于蓝色的百科全书
|
北京白癜风专科医院在哪里 http://m.39.net/pf/a_4540751.html ? 文=卡罗尔·梅弗著焦晓菊译 本文摘自《幽蓝之神:一种色彩的自我拆解》,由上海世纪文睿授权发布 如同一只长筒袜: 隐喻和转喻的两条路径 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lProust)对隐喻并不陌生。他的《追忆似水年华》(InSarchofLostTim)特别喜欢染有蓝色/忧郁的隐喻。 该书的第五部“女囚”充满了蓝色,在这里,我们跟“马塞尔”一道,追求他那位难以捉摸、充满魅力但又平淡乏味的阿尔贝蒂娜,但对他来说,她是不可能被俘获的。她就像水一样溜过他的手指。阿尔贝蒂娜是大海(隐喻地说),一切都在她那海滨似的虹膜里面。普鲁斯特写道: 她那双细细长长的蓝眼睛——现在更细更长了——有点变了模样;颜色依旧没变,但看上去就像是一汪清水。以致当她闭上眼睛时,你会觉得就像是合上了一道帘 幕,遮蔽了你凝望大海的视线。 正如那位伟大的比喻学家海登·怀特解释的那样,“隐喻意味着‘任何跟相似性有关的’东西”。就像从阿尔贝蒂娜眼中倾泻而出的大海(或者就像将一只长筒袜套到一条匀称的腿上),隐喻即扩展。 一只蓝色长筒袜 小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制作氰版物影照片(不使用相机拍摄的照片)。我们将一张张深蓝色的感光纸放在明亮的阳光下,再把各种物品如帽子、短袜、花或奥菲莉娅那样用树叶编的花环直接放到纸上。然后我们便等着它在阳光照射下差不多变成白色。 这大概需要五至七分钟,具体取决于阳光的明媚程度。接下来,我们就可到厨房水槽或浴缸的水里显影。望着蓝色消退然后重新出现,就像将颜色不断变化的天空拍成电影再快放出来,这时我们会看到,刚刚放在感光纸上的物体作为精致的“白色负片”,神奇地显现出来了。 安娜贝尔·多弗,《无标题(冲洗一张氰版物影照片)》,年,摄影。 安娜贝尔·多弗(AnnablDovr)采用了同样的制作过程:她将一顶帽子、一只短袜、一朵花、一个奥菲莉娅那样的树叶花环或一只长筒袜放在氰版感光纸上。多弗的“长筒袜”形象体现了蓝色作为扩展的隐喻和转移的转喻,而且也诙谐地挖掘了“蓝袜子”一词的负面与正面意思的矛盾之处。 “蓝袜子”的标签最初被用来指称知识分子,男性和女性都包括在内。18世纪之后,“蓝袜子”就只用来表示博学的女性了。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干脆把女学究称为“蓝袜子”,由此成为聪明女性的贬称,她们由于智力出众,由此也必须邋邋遢遢,喜欢精纺的蓝色长袜甚于丝袜。“蓝袜子”是个由褒义词变成的贬义词。 多弗的蓝色长筒袜当然是丝袜:它的透明构成了这幅氰版物影照片的美感。紧密的黑色接缝原本是“负面”的阴影,在照片上却作为“正面”的白色曲线显示出来,精致而细腻,就像蛋糕上的装饰花边一样。这只长筒袜薄如蝉翼,非常性感,那条绝妙的接缝线一直延伸到大腿后部。它属于这位艺术家的外祖母,后者将它精心保存下来,预备穿上它迎接丈夫从“二战”中返回家园。 但她的丈夫一直音讯全无。他再也没有回来,估计已经阵亡。 那位外祖母后来再婚,嫁给了一个可怕的恶棍。但她仍然怀念自己失去的丈夫。这位精力充沛的外祖母,对自己失去的第一任丈夫念念不忘,便将自己这双性感的长筒袜(其中一只被多弗用来制作氰版物影照片了)以及一条漂亮的丝绸手绢、若干红色的唇膏存放在一个一直紧锁的抽屉里(到她于20世纪80年代末去世后才打开),她以恋物的方式,纪念自己所失去的。 但这个紧锁的抽屉(以及里面放的长筒袜、手绢和唇膏)并非其恋物癖的唯一表现。外祖母去世后,在她的皮衣衬里内,还找到了一条缝在里面的粉色丝质衬裤(是为她失去的丈夫留的)和他的照片。(多弗根据外祖母那条塞进皮衣衬里的粉色衬裤,而将她称为一尊活生生的梅拉·奥本海姆[MértOppnhim]雕塑。)要等到多弗的母亲整理外祖母的遗物时,才会发现这些小小的“战利品”。 在检查那件皮衣的口袋时,她隔着缎子衬里摸到了那张照片和粉色的丝质衬裤。有时你会感觉自己失去了什么,却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寻找它。这是多么绵长深切的相思啊。 安娜贝尔·多弗,《无标题(长筒袜)》, 年,氰版物影照片。 多弗的蓝色长筒袜漂浮在一片蓝色的大海中,就像奥菲莉娅漂在河上: 她的衣服舒展开 将她托在水面上,那时她就像条美人鱼。 那只长筒袜漂浮着,强调了那位外祖母悲剧人生中的细节。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女主人公“掉进呜咽的小河”,多弗的外祖母也死在水中:她在凉凉的浴缸里突然心脏病发作,于是,奥菲莉娅被多弗的外祖母取代了,而这两个女人又被前拉斐尔画派的模特、艺术家兼诗人伊丽莎白·西多尔(ElizabthSiddall)所取代。 当约翰·埃弗里特·米莱(JohnEvrttMillais)为莎士比亚最有浪漫色彩的女主人公创作那幅《奥菲莉娅》(Ophlia;–)时,她因为给这位画家当模特而闻名。值得注意的是这位模特因此患上感冒的故事。 实际上,当西多尔像奥菲莉娅那样,漂浮在一个为画室精心设计的临时河流(其实是个浴缸)上时,下面的加热灯熄灭了。西多尔被冻得够呛,但她却默不作声。结果,她因此而染上重病,差点死去。 这两位奥菲莉娅——伊丽莎白·西多尔和多弗的外祖母——构成一部令人寒气透心的传奇“神话”。她们俩似乎都在说:“将我带走罢!”正如美国诗人娜塔莎·特雷塞维(NatashaTrthwy)写到西多尔染上感冒时说的那样: 在米莱的画中,奥菲莉娅仰面朝天而死去, 她睁大眼睛,张开双唇,仿佛在吐出 自己的遗言或最后一口气时卡住,花朵与水草 从池子中生长出来,漂浮在 她周围的水面上。那位充当模特的年轻女子 在浴缸中一躺就是几小时,哆哆嗦嗦, 染上感冒,也许正想象着鱼儿 缠在她的发丝中,或轻咬一颗 从她苍白肌肤上冒出的黑痣。奥菲莉娅最后的目光 注视着天空,她蜷曲的手掌张开 仿佛她刚说了一句:将我带走罢。 米莱画中的奥菲莉娅通过花朵——尤其是那些蓝色的——讲述了相思成疾的神话。看看那只环绕西多尔脖子的花环,用泛蓝的紫罗兰编成(如同一根套索)。顺着河岸寻找那些蓝色的勿忘我。注视着撒在西多尔金色的裙子上的那些蓝色的三色堇,“它代表了相思”。 将多弗的蓝色长筒袜理解为像奥菲莉娅那样漂在水上,这是隐喻,是在提出问题,“‘这是什么?它有什么含义’——这是批评与哲学写作的真正问题(巴特如是说)”。 伊夫·克莱因,《蓝色时代的人体测量》 (Anthropométridl’époqublu),年, 用纯颜料和合成树脂绘于纸上并用画布装裱。 将多弗的蓝色长筒袜解理解为她的外祖母则是转喻,是在“提出另一个问题,‘在我说的话后面紧跟着的会是什么?从我讲述的插曲中能生发出什么?’:这是长篇小说的问题(巴特如是说)”。对巴特而言,哲学是隐喻,长篇小说是转喻。巴特就像普鲁斯特一样努力从事这两方面的写作,因此就像多弗的蓝色长筒袜一样,是个“隐转喻”。 这只长筒袜就是奥菲莉娅(隐喻)。这只长筒袜就是失落(转喻),它是那个失去的丈夫;它是那位外祖母欲望的转移。她思念他。它是一个被割裂的主体——正如这本书,正如蓝色。 漂浮的蓝色世界 世界上出现的第一批照片中有一些是蓝色的。年,约翰·赫歇尔爵士(SirJohnHrschl)发现了制作氰版照片的过程。他用它制作蓝晒图,以保存各种票据和图表的副本。但是安娜·阿特金斯(AnnaAtkins)将这种技术用于摄影,制作她的一系列数量有限的书籍,上面用令人惊艳的伊夫·克莱因蓝记录了植物标本的图片。 安娜·阿特金斯,双叉网地藻(DictyotaDichotoma), 自《英国海藻:氰版物影照片印象》 第一辑,年,氰版物影照片。 年,安娜·阿特金斯的罂粟神奇地出现在如一池碧水的氰版感光纸上。 当阿特金斯的罂粟在湿漉漉的水池中显影,慢慢呈现在她面前时,这个迷人的过程让人想起普鲁斯特自己那些不可思议的日本纸花: 就像日本人爱玩的游戏一样:他们抓起一把看似没有明显区别的碎纸片,扔进一个盛满清水的瓷碗里,碎纸片着水之后便伸展开来,出现不同的轮廓,泛起不同的颜色,千姿百态,变成花……同样,那时……维福纳河里漂浮的睡莲……还有贡布雷的一切和市镇周围的景物,全都显出行迹,并且逼真而实在……都从我的茶杯里脱颖而出。 马塞尔那些逐渐成形的花朵和睡莲,以及他童年时代在贡布雷留下的无数其他的回忆,都暗示了那一刻的“悠闲”,被巴特当作“写作的时刻”而标记出来。正如巴特所写的那样,“那些日本纸花紧紧折拢,在水中盛开、舒展。那算得上悠闲:是写作的时刻,是工作的时刻。” 年,安娜·阿特金斯制作了一本海藻的书。漂浮的海藻就像“雏菊的泡沫”,被翻滚的海浪冲上岸来,是大海讲述的短篇小说的碎片。“海藻”一词的英文“alga”在拉丁语中意为“海草”,其语源已不可考。很可能这个词源自“alliga”,后者的意思是“捆绑与纠缠”,16听起来就像书页上的字母,只是原本蓝色的墨水是白色的,而原本白色的书页却是蓝色的。 安娜·阿特金斯,海藻地衣(LichinaConfinis), 自《英国海藻:氰版物影照片印象》第一辑,年,氰版物影照片。 海藻的故事包罗甚广: 有些形如羽毛,例如酸藻(Dichloriaviridis)。 奇怪的是,有些也颇具现代感,例如束状海带(Laminariafascia)。 有些就像击中大地的一道断裂的闪电。 有些像简笔画。 有些像陈旧的圣诞树,枝残叶败。 有些像正在缝纫的线。 有些像磨损、残破的缎带。 有些——例如网状翅藻(Halysrispolypodioids)——像浑浊 的树胶水彩画,由于 它不透明,像树胶水彩画甚于水彩画。 有些像压成标本的旱金莲花朵,例如粉团扇藻(Padina pavonica)。 同样是粉团扇藻,有些却像贝壳的碎片。 有些像花椰菜。 有些像金属的榴霰弹。 有些像炸裂的小洋葱。 有些像长长的卷发,是从某个女人用了一个星期之后的 梳子上扯下的。 有些像我六岁时放置在厨房窗台上、 盖有纸巾的玻璃杯里生长的豆类的根。 有些像大量的狗尾草。 有些像一个古怪的法文字母,印在20世纪40年代的丝绸衣服上。 安娜·阿特金斯,疣粒链藻(CystosiraGranulata), 自《英国海藻:氰版物影照片印象》第一辑,年,氰版物影照片。 纸张如奶油。 点叶藻(Punctarialatifolia)就像个肉感的小女人,穿着 几乎透明的衣服站在太阳底下,等待公交车。 它们有点像进行罗夏墨迹测试。 厚点叶藻(Punctariaplantagina)就像个基迪拉克人。 其中一种像我母亲那只尼龙袜,被揉得皱巴巴,丢在一旁, 恰如20世纪60年代的很多家庭主妇感觉的那样。 有些像丝茧。 有些像一颗被吹散的蒲公英种子。 有一种像我祖母的胸针。 有些像一堆堆的泥土。 有些像小小的珊瑚碎片。 有些像松软的特尔斐长裙透明的褶皱, 由马里亚诺·福迪尼·马德拉索(MarianoFortunyMadrazo) 生产,例如球根海带(Laminariabulbosa)。 阿特金斯的《海藻》特别有海洋学(海洋写作)的感觉。就仿佛她是从海里直接捞出那些标本似的,这些“海中花朵”在一片片如水的蓝色中重新绽放在我们面前,似乎不由自主地悬浮在一个不受时间控制的漂浮世界里,就像“那些日本纸花紧紧折拢,在水中盛开、舒展……是写作的时刻,是工作的时刻”。 《幽蓝之神:一种色彩的自我拆解》 [英]卡罗尔·梅弗著 焦晓菊译 上海世纪文睿出品 作者简介卡罗尔·梅弗是曼彻斯特大学艺术历史与视觉研究专业教授,师承世界著名文化史大师、后现代历史叙事学重镇海登?怀特(HydnWhit)。已出版:《稚气地阅读》()、《黑与蓝》()。 ? 本文由腾讯文化内容合作方授权发布,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zw/5658.html
- 上一篇文章: 红梅赞一首革命歌曲,视频,伴奏,曲谱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