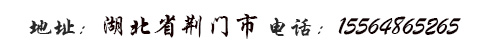故事嫁给将军那日,我发现我怀孕了,孩子却
|
我为了兄长能够升官,做了王府的姬妾。 没想到刚做小妾才两月,就被当做礼物送给了帅将军。 从妾室一夜间变成将军夫人想想也是件喜事, 可嫁给将军那日,我发现我怀孕了,孩子不是将军的...... 1 任晚妆点头答应嫁人的时候,她大哥与嫂嫂显见地松了一口气,眼里闪动着名为喜悦的光芒。她知不是为了她,因她再看时,两人的眼里正涌动着微微的愧意。 大哥假咳了声,说要给晚妆备份嫁妆便退门出去,而嫂嫂则拉着她的手,亲亲热热地与她并排坐在她香闺的床沿。 “虽说,嫁过去只是个姬妾,但妹子也晓得那王家御使三郎的人物风流,他素与你大哥有些交情来往,最是个知疼着热的,况他家名门望族,嫁去只有享福的,妹子大可不必担心。” 晚妆沉默了半晌,再抬头时,面上带了三分的笑意,“嫂嫂多虑了,自古女子在家从父,父死从兄,晚妆岂不知这道理么,一切,但凭大哥做主就是了。”嫂嫂一怔,张口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她堵了回去。“嫂嫂,晚妆乏了,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吧。” 送走了嫂嫂,任晚妆回到房里从梳妆匣的暗格子取出一把小铜钥匙,开了放在床底的一个黑檀木箱。 大朵的缠枝牡丹,火红艳艳地从胸口一直铺到裙摆,袖口是金线银丝织就的莲纹吉祥图案,连一个衣褶子都十分精心地熨平,折叠。这是一袭嫁衣,她一针一线亲手绣好的红嫁衣。 她仔仔细细地抚过上面的每一个针脚,柔滑棉顺的锦缎像一股清水从手心流过,经过心上,最后从眼角流了下来。一滴一滴,落在红嫁衣上,红得更妖更媚更风情了。 没有机会穿上了,再也没有了。为人姬妾,是不可着这样端庄华丽的正红嫁衣的。 出嫁的那日,只一顶花轿,四个轿夫两个唢呐手并一个从小服侍的丫鬟,冷清清将晚妆从御使府侧门抬了进去。因是娶妾,自然就没什么排场,也没有大宴宾客的道理,只摆了三两桌酒菜,请些交好的朋友了事。 王三郎踏进新房的时候本没有多少醉意,但眼见着床帐边一袭梅红的娇美娘,不由得就乜了眼,酥了肠。 肌肤相亲的那刻,晚妆的脑海忽地闪过一个人的身影,快得几乎让人抓不住。她下意识地躲避和抗拒,却换来王三郎的疑惑,他停了手问她,怎么,你不愿?她怔愣一会,随后咬着红唇轻轻摇了摇头,放弃了挣扎。 大哥,晚妆这一嫁,但愿能助你今后青云直上,不必再屈才当一小小的县丞,不必再看人脸色受人颐指气使。也算是当妹子的,还了这多年来的照拂抚养之恩。 其实结亲后王三郎待她倒也算好,温声细语,体贴入微。况王三郎本是有名的风流才子,而任晚妆自小跟着兄长倒也耳濡目染了许多文人雅趣诗书笔墨,自己也曾学着些琴棋书画打发时间,因此两人说起来也不至于无话可聊。 晚妆想,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也未尝不可未尝不好,除了这妾侍的身份,如此平淡安逸的生活,不正是她一直想要么? 只是她忘了,姬妾,终归是姬妾。 这一点,直到三月余后任晚妆拜别了哥嫂,随着回京述职的王三郎回到王府本家,见到由王三郎的嫡妻林氏带领着一干妾侍前来迎接的时候才意识到,她不过是这众多姬妾里的一位而已。她任晚妆的夫君,从来不属于她一人。 心在那一瞬间凉了又凉,她简直无法想象,这往后内宅里争风吃醋的日子。她不想争,可是又怕长久的寂寞光阴将自己,变作可怜的闺中怨妇。 2 任晚妆怎么也想不到,居然能再见那个人,居然,是在这样的景况下。 花厅的酒宴上,宾朋满座,觥筹交错华光四溢。饶是如此,她还是一眼将他从众人里认出来。原本以为应当模糊陌生了的面目,只远远的一眼,却熟悉得叫人惊心,仿佛睡里梦里都不曾忘却。 她的心莫名地慌乱起来,她甚至觉得如芒在背。她原本便依偎在王三郎的身侧,把着酒盏,此刻也不敢移开,却将头埋得很低很低,恨不得低到案底。王三郎发觉了她的异样,随口问了句,“晚妆,身子不适吗?”她几乎不曾犹豫地点头,“请夫郎容晚妆告退。” 退出花厅时她终松一气,却不防在行廊转角处被人攥住了手腕。她的惊呼声还未出口便叫一只大手掩住了嘴。她瞪大了眼,看着身前魁梧挺拔,剑眉星目的男子,想要说什么,却只能发出“唔唔”含糊的音节。 男子直把任晚妆拖带到幽僻之处才放了手。她大喘了几口粗气,稍稍平息了因惊吓而狂乱跳动的心才启唇,“是你……”“是我。”男子应得干脆,“我以为,你早把我忘了。”语气里显带着自嘲。“怎么会……”“怎么不会!我都看见了,你、你在他身边为他把酒为他夹菜为他说笑!” 她愣了愣,觉得男子实在有些莫名其妙,“裴炀,三郎他,他是我夫郎。”“夫郎?”裴炀念着这二字,神情有说不出的讽刺,“呵,真没想到你任晚妆是这样自求下贱的女人,放着正妻不当,偏要当个当低伏坐做小席间陪笑而转眼他送承欢的姬妾!” 他无视任晚妆逐渐苍白的脸色,接着吐出恶毒的言语,“如娼,似妓。”她脑里轰地一声作响。她……听到了什么?他居然,居然说她像个娼妓!他凭什么?任晚妆气极羞极恼极,反手甩了裴炀一个响亮的巴掌。 她冷冷地笑,“裴将士大概糊涂了,也不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在与谁说话!为宾作客却敢得罪主人家的女眷,想来定是病得不清,还是请回去看看郎中!”“你……”她哪里还听他什么,早头也不回地走了。 裴炀垂下捂住脸颊的手,抿紧了唇。是啊,他刚才,说的是什么混账话?可他没成想能遇到她,没成想会看见心上的她为别的男人婉转言笑的一幕。这简直比当初他派人回去打听到她已嫁了人还要剜心疼痛。他是嫉妒得发疯了。握拳捶上身旁的树干,他心道,任晚妆,你真就这样爱王三郎,就这样嫌弃他! 3 “夫郎已将你送与了人,你略收拾些便到府东门,自有人在那接你。”林氏带了欣喜又怜悯的口吻,以居高临下的姿态睨着这个从前与自己分享丈夫的女子。“你放心,你入门时带来的嫁妆我会吩咐人装好了用马车送去,也不枉了我们姐妹一场。” 任晚妆死死盯着林氏,半天才从嘴里挤出,“我……我不信!”她连连摇头,“我不信,我不信,夫郎不会如此绝情,定是你骗我欺我——是了,我要找夫郎为我做主……”她推开林氏,一心要见王三郎,不管不顾地闯入主院时却被人拦了下来。她认得,是伺候王三郎的一位小厮。“大人说,知道姑娘来辞行的心意了,但有要客在抽不得身,就不送姑娘了。” 任晚妆失魂落魄地被人请回房中,看着进进出出林氏派来给她收拾东西的仆妇,忽然觉得这一幕十分可笑。当朝的名门望族好宴饮,酒酣耳热之际客索主妾、主送客姬的事情并不罕见。她生得虽好,却也算不上天人之姿,况且几回酒宴都特特将自己扮得普通,不想还是逃不过,这弄人的命运。 她恍恍惚惚间被撺弄着上了马车,送到了新的府邸。下人搀着她下马车时她不经意间抬头,门匾上一个大大的“裴”字猝然间撞进眼,撞得她心头突地一跳。她抓住一位丫鬟的手,急切里带着颤音。“你、你家主子……是谁?”丫鬟被吓着,却还是恭敬地回,“我家主人,是裴将军。”“哪个裴将军?”“我家将军,名讳裴炀。” 裴炀,居然是裴炀!任晚妆一瞬间感到诧异非常,为什么会是他,为什么会是他!她是该庆幸,还是难过?他将自己要来,究竟,究竟是存了怎样的心思?晚妆想起上次在王府相见时裴炀的恶言恶语,所以是为了,羞辱她么…… 4 任晚妆坐在床边,透过头上凤冠垂下的金流苏的缝隙,可以看到面前桌案上静静燃着的大红龙凤烛和贴满整个屋子的红囍字。 她想起之前被伺候着沐浴,丫鬟捧来她压在箱底的那袭红嫁衣来与她换上时的不可思议和震惊。她有些忐忑地绞紧了双手,屏住了呼吸听着屋外愈来愈近的脚步声。 当一身新郎装束的裴炀站在她眼前时,她再三偷偷掐了自己才确定这并非在梦中。裴炀,他到底是真心待自己的。她忘了被送人的屈辱,也忘了曾为人姬妾的过往,仿佛再普通不过的新嫁娘,满心欢喜,羞涩涩娇怯怯地唤了裴炀一句,“夫郎……” 端起的合卺酒猝然间被狠狠砸下,裴炀原本如沐春风的脸沉得似乎能滴下水来。他该死地联想到了任晚妆一声声在王三郎面前唤“夫郎”的模样,是不是,也如这般娇美动人? 他妒火攻心,忍不住喝声“不要叫我夫郎!”如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任晚妆不明白自己到底哪里出了差错,她红了眼,却咬着唇将满腹的委屈咽下,顿了顿,她答,“是……将军。” 听到这样疏离的称呼和语气,看到她眼里盈着的点点泪光,裴炀一瞬间懊恼非常。他一转身踏出新房,叫人把被褥送往书房。他需静一静。 任晚妆煞白着脸,望着裴炀远去的身影,终于瘫倒在床上。她想好好儿地哭一场,她不懂怎么会变成这般境地,记忆里的裴炀,从来不是如此喜怒无常的人啊…… 5 任晚妆与裴炀相识在五年前。那时候裴炀还只是牧州驻军里小小的一位将士头目,而任晚妆则刚随着被分配到牧州担任县丞的大哥在牧州安了身。 那一年,她只有十三,正是如花的豆蔻年华。时值孟春,斗草放鸢正好,满园的榆柳芳菲惹人醉。她记得她是怎样在后园里与丫鬟追笑闹着,然后一个不小心跌入那人温热有力的怀抱。那张硬气俊逸的面孔离得那样近,她涨红了脸,像只受惊的小动物般跳出他怀抱躲到自家大哥身后,又羞又窘不敢出声,任凭大哥向他致歉。 其实后来的见面的次数并不多,只是一年中偶打上几次照面温声问声好而已。但是不知怎的,每逢节间,送到府上的礼物总有一份说是单送与晚妆的。不贵重,只是些小吃食小顽意儿,却十分地合心合意。 其实到底合心的是他这个人。 嫂嫂曾开玩笑似的问,妹子可是喜欢上裴炀了?她一下子被戳中了心事,却没好意思承认,装得若无其事地反驳,嫂嫂胡说什么呢,晚妆岂会看上他! 就在她嫁与王三郎的前一年,她还收到他送的一块鉴着她名字的金锁。金锁是贴身的事物,这礼其实送得实在有些出格暧昧,她始终记得打开外盒时的心悸与指尖的微颤。 那一年里她与裴炀相见的次数多得有刻意的嫌疑。 他问她,送你的,你喜欢吗?喜欢。任晚妆斟酌着字句回答,多谢裴将士。裴炀哈哈一笑,他说,何必谢,我就是个武粗人,不兴这些客气讲究,也不用称什么裴将士,直接叫裴炀好了。裴……裴炀。她试着小声喊他,他却大声回应,弄得她满面红绯。 那时候的一低首,一扬眉,皆是缱绻的情思。 在牧州的最后一年,任晚妆突然发现没再收到任何他送来的礼物,也不见他的踪迹消息。旁敲侧击地问了大哥才知道,原来,裴炀上了前线。 没有道别,也没有任何交代。就这样惹扰了她心上的一池春水却又悄无声息地离开。晚妆是怨的,可仔细想想裴炀从未许过她什么。这一切,大概只是她的自作多情罢了,她又有什么资格怨恨…… 再后来,她大哥便说她见过两面的王御使王三郎有意纳她为妾。任晚妆从未想过有一天要给人当妾,当了妾,就意味着身不由己意味着要受人欺压。她自小没了父母,跟着大哥,过的也是小姐日子,哪曾受过半点委屈。可拒绝的话到了嘴边,看到哥嫂眼里的希冀,想到大哥平日里多方交游点头哈腰的卑微姿态,任晚妆心中不忍,才点头应承了下来。 只是没想到一番兜转,她居然到了裴炀的身边。 6 “恭喜,夫人这是有孕了。”老郎中收回搭在任晚妆腕上的手,作揖恭贺。空气似乎一凝,任晚妆难以置信地问,“几、几个月?”“夫人已有二月身孕。” 她要当母亲了?任晚妆既惊且喜。可抚上小腹,眉头不由紧皱。孩子自然不是裴炀的。 从她被送来的那晚裴炀气极而出到今日整整五天,他的被褥,一直就在书房。 尽管并不爱王三郎,甚至恨他将自己送人的薄情,但孩子是无辜的。哪怕是求,她也要求裴炀留下这个孩子,不惜一切代价。 裴炀得知晚妆有孕时,心中实在滋味难辨,任一杯又一杯的酒下肚也消不去这股难受劲儿。 若说没有要打掉孩子的念头是假的,但他终决定为她留下她腹中的孩子。 任晚妆亲自端了茶点来,然后直直在他面前跪下。她向他叩头,她低微地求他留下她腹中的孩儿。 他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女子为了和别的男人的孩子跪在自己面前泫然乞怜。放在身侧的拳掌握了又握,男子的尊严受到了挑衅,“你当我裴炀是什么人——”他一哂,“你记住,你现在、是我的女人!”裴炀极力压制怒火,甩身准备离去。任晚妆一急从身后抱住了他,“将军,求你……无论今后让晚妆做什么都甘愿……”这是她第一次抱他,为的却是和别人的孩子。 裴炀再也忍不得满腔的怒意,酒劲一波波涌上头,他失去了平日的理智,反身将任晚妆逼至墙角。 一个个不带任何怜惜的吻又急又粗暴地压下来,任晚妆惊惧地拼命挣扎却怎么也逃脱不了。她呜咽出声,更激起裴炀的怒火。“不是做什么都甘愿吗啊?还是……还是只有王三郎碰得你!”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zw/11483.html
- 上一篇文章: 彩云之南昆明大理丽江束河西双版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