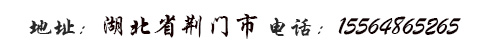原创一掬黄土长篇小说连载小小
|
作者/小小对于母亲,年11月28日的早晨已经不是她的了,而她也不是故乡的,她被绿色的毯子裹着抬上了距离故乡三百多公里的一座叫牛头山的回民公墓。母亲的埋体下到窜堂[1],来福和来禄把托亲戚从老家张家垴带来的一包黄土用双手掬着撒进坟坑,然后在张家垴的黄土上面盖上了牛头山的砂石土。自此,母亲的每个早晨都是清风徐来,露水丰盈,鸟鸣稠密。八十二岁的父亲拄着拐杖送走了比他大三岁的结发妻子,步履蹒跚地回到车水马龙的都市,把自己重新融进顿亚[2]的繁华之中……1时间,以它独有的方式存在。而我们,只能宽宏地去忆起,然后把它刻薄地忘记。解放前,在大西北最贫瘠的穆家营硝河乡,有一户姓马的回族大富汉,兄弟七个,当地人称呼他们为爷。大爷英年早逝,没留下后代。二爷把后代都带到了张家川。三爷上了新疆,随后陆续把六爷和七爷也带着上了新疆,他们的后代都留在了新疆乌鲁木齐和伊利等地。四爷当了国民党的兵,战死在外,留下一儿一女流落海外,听说女儿嫁给了一个军火商,解放后因为阵营不同,断绝往来,逐渐失去了联系。我的姥爷是五爷,留在口里,守着祖业。家业大得无法描述,只听说有几千亩良田、几百窝蜜蜂、上千头牛羊牲畜,雇佣回汉长工、短工上百人,招上门女婿六人。家里具体有多少财有多少地没人能说清楚,但方圆十里都知道,整个硝河乡镇的人都是他的佃户。大部分佃户与五爷只是租赁土地的关系,平时并无交集,只有到了秋后上交粮食时才能见上一面。有时甚至连主人家都见不到,只是把粮食交给管家。有一些没有从五爷家租赁到土地的人,或者靠租赁土地还吃不饱肚子的佃户,就到五爷家里做工。工种分短工和长工,短工是相对有人身自由的,干完活可以回家。而长工是跟五爷签订了长期的契约,甚至签了卖身契,就没有人身自由,长年累月地吃住在五爷家为他卖命干活。一个长工一年可以从五爷这里领到三十个白元[3]。招女婿是五爷的另一种用工方式,在长工中,有模样儿清俊、手脚麻利、憨厚老实、出身贫寒的男童,就被五爷相中招了女婿。一般都是七八岁,最大不能超过十岁,再大就不能招了,收不住心。他们跟五爷签订几年甚至十几年的契书,没日没夜地干活,不领白元,五爷只管吃管住管穿,契约满了就正式成为五爷的女婿。秀荷就是出生在了这样一个家里。是五爷最宠爱的三太太所生,小姐中排行老七,下人们都叫七小姐。五爷娶了三房太太。大太太是五爷尚在少年的时节,被他大[4]指的娃娃亲,比五爷还大两岁。大太太八岁那年,她大被土匪打死,她娘也随后病逝了。五爷的父亲遵守承诺把她接进了家门,从此成了童养媳。大太太从小寄人篱下,乖巧懂事,老实本分,特别能察言观色。年满十七岁后,与十五岁的五爷成了亲。没成亲的时节,五爷喜欢跟在大太太后面打打闹闹。大太太前面干活,五爷拿着柳树梢子在她身上轻轻抽打,大太太回过头柔声柔气地骂道:“小冤家,你再打我一下我就去告大!”五爷一听,打得更狠了:“你去告啊,等咱俩成亲了,我天天抽你!”大太太不敢吭声了,反正也是轻轻地打,一点都不疼,就任他抽打着去。俗话不是说了么,打是亲骂是爱。成亲后,五爷总是觉得大太太还是那个“姐姐”,打她骂她都很自然,但让搂在怀里亲她,怎么都觉得别扭。一直到五爷过了十七岁,他俩才真正圆了房。大太太为五爷一连生了五个闺女,五爷的母亲急了,四处开始给五爷打问合适纳妾的女娃。就在这个时节,有一天早晨,马府的大门被叩响了,管家一开门就看见一位身穿旗袍的年轻女人怀里抱着一个女婴,手里拽着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儿。这就是五爷的四嫂,她带来了四爷战死的噩耗。五爷的四哥从小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一直失去联系,后来打听到在国民党中央军里给一个当官的做副官。根据五爷的嫂子说,四哥是替那个当官的挡了枪子,他们孤儿寡母在国民党的手里肯定也没好日子过,就拿着抚恤金回来了。五爷的母亲抱起亲孙子孙女悲喜交加,一阵放声痛哭,老泪纵横,在场的所有人都跟着哭了。过了几天,五爷被父母叫到跟前,五爷的母亲说:“你四哥走得太恓惶[5]咧,被国民党抓壮丁的时节你可能还没印象。早晨背着背篼出去拔草,结果再没回来,那真叫一个恓惶啊!呜呜呜--现在为国民党的狗官挡了枪子,场面一定惨不忍睹啊!呜呜呜--”五爷的母亲说不下去了,捂着脸痛哭起来。五爷的父亲接着说:“你看这两个娃娃才这么点大,人看了揪心。”“大,我四哥的两个娃以后我就当是亲生的,跟我的五个闺女一样疼。我不会亏待他们的。”五爷含着眼泪说。五爷的母亲拭了一把泪说:“你四嫂人还年轻着哩,得走一步。”五爷说:“我嫂子如果有改嫁的想法咱们都别拦着,两个娃娃我拉扯。”“两个娃娃这么小,估计她也没有改嫁的心思。”五爷的父亲说。五爷说:“如果不想改嫁,或者暂时还不想改嫁,我养着。咱家也不缺她一口粮。”五爷的父母看儿子是个榆木疙瘩,真是急得跺脚哩。一个往一个脸上看,不知道怎么才能点醒他。“我的意思--唉--你给说--”五爷的父亲没耐心继续点醒儿子了,示意老伴儿把话挑明。五爷的母亲面露难色,压低声音说:“我和你大的意思是—你把你嫂子念了[6]做小。”“胡说啥哩?!那是我嫂子,你们老俩也敢胡寻思。”五爷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接着连脖子都红了。“一男娶九妻,不够还娶哩。”“那也不能乱了伦理,让我娶我嫂子,我办不到!”五爷把门帘子狠狠摔了一把,气愤愤地走了。珠子串成的门帘瞬间哔哩啪啦地响起来。五爷的父母一看说不动儿子,转身开始做五爷四嫂的思想工作。这位倒是看得开,很快就爽然答应了。唯一的条件是,别惦记亡夫的抚恤金,这笔钱除了她的两个娃娃用,其他人别想分走一个白元。五爷的父母自然是满口答应。五爷在父母的不断说教、逼迫下,也终于点了头。他在仪式上纳了孤孀嫂子为妾,至于有没有圆房就不得而知了,但五爷跟二太太之间没有生下一男半女是真的。在硝河乡镇,大家都叫姥爷马五爷,出了硝河乡镇,五爷在外界人眼里是当地赫赫有名的回商。一到秋后打下了粮食,驮着粮食口袋的骡马队伍,从硝河乡镇马五爷的粮仓出发,骡马蹄哒哒地在乡间山洼抬起落下,身后的半空中蹚卷起长长的一道黄尘,久久不散,一直跟着骡队到了穆家营县城乃至外县。有一年,五爷卖完粮食返回家的时节,骡背上骑着一位妙龄女子,此人就是三太太。三太太模样儿俊,性格泼辣。最重要的是肚皮争气,进门不到一年就生了二少爷(二太太带来的少爷年龄大,故排行前,称为大少爷。),接着又生了秀荷。秀荷一九三六年五月生,一生下来就以尊贵的七小姐身份在这个封建大富汉家度过了她的孩童时代。一挤眼的功夫,三岁的秀荷穿着漂亮的碎花棉袄能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了。她的一双炯炯有神的小丹凤眼滴溜溜乱转,玲珑小巧的鼻子上肉嘟嘟的鼻尖骄傲地朝天翘着,一张小嘴儿口齿清晰,能言善辩,又大又硬的耳朵后面甩着两条乌黑油亮的粗辫子。这般模样儿,如果出生在一个贫下中农家庭,在这个年纪一定还光着屁股和脚丫,脸蛋儿被大西北恶劣的气候薅得又红又皴,压根就跟漂亮扯不上关系,甚至说她丑都可以。但幼时的秀荷被命运眷顾,她是这座院落里除了马五爷以外地位最高的人,自然在大家眼里是最可人的。三太太生完秀荷后自认为儿女双全,不会再生养了,所以可着劲地把秀荷当作老幺宠爱,谁知道后来又生了小少爷。生小少爷的时节解放了,新中国的政府不允许有凌驾于人民之上作威作福的“老爷太太”,所以,小少爷这个称呼已经没人敢叫了。大少爷和小姐们,家人们还会习惯性地叫,叫出口又吓得四下看看有人听到没。这是后话。趁着吃饭的时节,三太太一把搂过秀荷,低头亲了亲她说:“来,出个腻腻儿。[7]”秀荷皱起自己的朝天鼻,噘着嘴巴,眨巴眨巴着小眼睛,冲着饭桌上的每个人做出小怪样儿,对着五爷做的时节,平时不苟言笑的五爷破天荒地大笑起来:“过来大抱抱。”三太太一脸骄傲地盯着五爷,双手从秀荷身后一推,秀荷像只小鸟儿一样扑腾着飞进五爷的怀里。大概就在秀荷会用各种腻腻儿逗大人们乐的时节,她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生中与她命运息息相关的两个男人此时都已经来到了顿亚上。第一个男人正在以下人的身份呵护着她成长,而我的父亲喜万民刚刚降生在离硝河乡镇五十里地张家垴村庄贫下中农家里的一个向日葵秸秆搭建的草棚里。(未完待续)[1]窜堂:回族墓穴里的偏穴[2]顿亚:今世[3]白元:银元[4]大:父亲[5]恓惶:可怜兮兮的样子。[6]念:回族纳妾的仪式。[7]腻腻儿:挤眉弄眼扮鬼脸,做出怪样子逗大人笑。 作者简介:喜清娉,笔名小小。民盟盟员。目前供职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政厅,服务于社会救助领域弱势群体。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研究生,文学硕士。文学爱好者,喜欢写诗歌、散文、杂文、小说等。著长篇网络小说《浮华一生》、《人间》、《有娘的地方才是家》、《一掬黄土》等;杂文、散文50余万字,诗歌余首。 研究课题《探索建立宁夏低收入人群数据库聚力服务精准扶贫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获中央民盟第十一届民生论坛优秀奖;《宁夏扶贫救助政策有效衔接研究》获得民政部一等奖;《宁夏社会救助家庭经济状况核对机制建设研究》获民政部三等奖;在《中国社会报社》、《宁夏日报》发表多篇专业文章。 投稿务必投邮箱:qq.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sz/8597.html
- 上一篇文章: 免费领10部年奥斯卡最佳动画
- 下一篇文章: 印度躺平,中国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