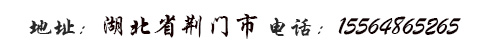伟大的文学都是反讽性的,米兰middo
|
北京哪个皮肤病医院好 http://baidianfeng.39.net/a_zhiliao/150708/4652392.html“在被遗忘以前,我们会变为媚俗。媚俗,是存在与遗忘之间的中转站。”我一生的雄心就是将最为严肃的问题和最为轻松的形式相结合。这不是纯粹的艺术野心。轻佻的形式结合严肃的对象立马就曝露出戏剧的真相(床上事和我们在历史大舞台的演出)和它们可怕的无意义。我们体验着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我的每部小说都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玩笑》或《可笑的爱》来命名,这些标题之间可以互换,反映出那些为数不多的主题。它们吸引着我,定义着我,也不幸地限制着我。除了这些主题,我没有其他东西可说或者可写的。 米兰·昆德拉(MilanKundera,年4月1日-),当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生于捷克,一生跌宕起伏,极富传奇色彩。年第一部长篇小说《玩笑》出版获得巨大成功,年移居法国,多次获得国际文学奖,并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代表作品有《玩笑》《生活在别处》《笑忘录》《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和《不朽》等。 米兰·昆德拉:人类一媚俗,上帝就发笑 米兰·昆德拉:面对现实的重复,思想最后总是缄默不语 米兰·昆德拉:对一个没有幽默感的世界感到恐惧 在诺贝尔文学奖将来的历史上,米兰·昆德拉的名字很可能与乔伊斯、博尔赫斯和纳博科夫摆在一起。这些同样伟大的作家有一个共同点——都被诺贝尔文学奖错过了。 政治liu亡者、文体创新者、极q抨击者、个体与人类命运关怀者,无论从哪方面看,现年92岁的昆德拉都是完美的诺贝尔奖候选人。 年,昆德拉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说,当瑞典来使告诉他的同胞、83岁的捷克“国家诗人”塞佛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时,塞佛特正躺在病床上,长久地盯着对方,然后忧伤地说了一句:但是这些钱对我又有什么用呢? NicerOdds网站年诺贝尔文文学奖赔率榜 在诺奖候选名单上,包括村上春树、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恩古吉·瓦·提安哥、玛丽斯·孔戴、哈维尔·马里亚斯、科马克·麦卡锡、唐·德里罗、斯蒂芬·金、玛丽莲·罗宾逊、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托马斯·品钦、安妮·卡森、安东尼奥·洛博·安图内斯、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牙买加·金凯德、查尔斯·西米奇、穆卡松加、林惇·奎西·约翰逊、理查德·奥斯曼…… 后现代文学档案 唐诺:米兰·昆德拉还在意诺奖吗? 《庆祝无意义》薄薄小说出版后,中国读者褒贬不一。不是谁都能看得懂。有人觉得昆德拉的小说10年并无进步,但是台湾文学评论家唐诺不这么看。 文/唐诺 从文学自身来看,诺贝尔奖其实一直是保守的,乃至于平庸的 我的老朋友,也是当前我最信任的文学理论者黄锦树,先我一步买了昆德拉的这本新书《庆祝无意义》,他把封面贴脸书上或许是提醒那几个应该读的人,还写下这两句乍看很激烈但其实只是简单事实的话——早该把诺贝尔奖给他了,阿猫阿狗都得了。 完全同意,而且不是现在才同意,我已经同意很多很多年了。不要昆德拉,也一直没要乔伊斯、普鲁斯特、格林、博尔赫斯、卡尔维诺和纳博科夫,神准到仿佛一再故意躲开,这难以用失误来解释了,所以里面必定有某些很稳定很确实的东西——纯粹从文学自身来看,诺贝尔奖其实一直是保守的,乃至于平庸的,仍服膺着某种集体逻辑(从外部作业到内在心理、思维),基本上,较合适它的是那些不错的二级作品和书写者,它不太敢要、甚至畏惧那些一下子超过太多走得太远的东西,那些太过复杂以至于无法顺利安装回当前人类世界的东西。那些难以在第一时间就获得至少某一种“政治正确”名目的异心东西。 只是,这个保守往往被它另一种选择给遮挡住了,那就是诺贝尔奖会,而且经常性地赠予那些或激烈挞伐某个世俗权势,或不公平承受着某种苦难,或安静入山中无日月地书写于某处世界边缘(小国、小乡小镇、或主流思维的远方)仿佛不思世俗眷顾的作品,然而,不从浅薄的世间权势而是从更宽广的人类真相来看,这些当然都是“更正确”的东西(肖比直接背反,对抗世俗权势更明白无误的道德正确吗?),这样的书写在世俗权势世界里也许(只是也许,看地区看情形)是危险的或寂寥清冷的,但在文学里更多时候是很安全而且容易的,甚至就在正中心,它们被道德温馨的一整个包裹起来,在道德大地的松软沃土上愉悦生长,而且长起来很快。事实上,如今已进展到栽植了,已经可以是一种书写策略了(需要列一张名单吗?)。 真正的文学书写当只是这样,博尔赫斯讲:“我不是一贯正确的,也没有这个习惯。”这样,我们就多听懂了这话的另一层深刻意思——文学当然有它自己的目标及其关怀,独特的、延续的、专注的,有它源远流长一直在想在处理的东西,不会和现实世界一致,否则文学干吗存在呢通过文学所获取的东西,或如昆德拉强调的,只有文学才能获取的东西,因此不会只单调地和现实世界背反而已,更多时候是岔生的,四面八方飞出去。 米兰·昆德拉还在意诺贝尔奖吗? 因此,昆德拉本人还在意诺贝尔吗?我们不知道但猜想这只是他多少得忍受的骚扰,一年忍耐一次(颁奖前后总有好事的人和不平的人如我们这样;之前,格林一直忍受了二十几次),但小说本身看起来完全不在意——在意的,如排队等着领圣餐的小说绝不会长《庆祝无意义》这样子,我们谁都知道昆德拉更加知道。 它会很厚,题材看来很大或至少以某种虚张声势的框架和语调来写,像猫要威吓对手(评审、评论家、读者以及同业)会所谓“宽边作用”的横身过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大;它会积极地表现“创新”,以各种敲门但并不必要的,甚至有碍作品的技艺演出或题材选择方式(比方不惜选择自己不关心不熟知的题目),好让作品拼图般横向展开看起来覆盖更广……它甚至会不太像是一个人的作品,而是一大群人,一个国族乃至于一整个时代的集体声音,并依此进行现实动员(评论界、文学界乃至于国家,作为一种仿佛可均沾的共同荣光),这些都是我们已一再看到的事实如此。 小说家的作品是一段时间的总结 昆德拉的书写是直向的,头也不回而去,这一指向愈来愈清晰——不自这本《庆祝无意义》始(中文版本字大行稀只页,估算不到四万字),昆德拉这么写已多年了,小说愈前行愈集中愈专注如一束光,除了持续想下去不再携带(或说一路卸下)额外加挂的其他目标,小说仿佛逐渐成为书写者身体的一部分,只讲自己必须讲的话,惟不只是结语,还有更多不怕显露失败但或许更加重要的矛盾,困惑不解及其试探,从这里得到一种不断回返核心,一种几乎绝对性的精准(以及一种事物更惊喜移动、晃动呈现的朦胧); 但从另一面说,这不是书写者放纵的一人喃喃自语,这是一部确确实实的作品,作品对昆德拉来说是这样:“所谓的’作品’并非指一个作家写出来的一切东西,连书信、笔记、日记都涵盖进去。作品只指‘在美学的目的中,一长段时间工作所获致的成就。’我还要更深入地说:‘作品’就是做总结的时刻来临时,小说家同意拿出来的东西……每个小说家都应该从自身开始,摒弃次要的东西,时常督促自己、提醒别人什么是‘实质核心的伦理’。” 这本四万字不到的小说于是牵动着太多,像生长在“路的末端”。根已伸得太长太深。往往,小说中的两句对话,或一小段描述,我们自信看,其实都不是现在才说的,要真的掌握它们(至少)得寻回昆德拉一整叠之前的作品才行,包括小说和论述(如《小说的艺术》、《帷幕》、《相遇》等),它们只是上一本书到这本书这段时间里又获致的成果,是上一本书结束后的“所以呢?然后呢?”。 但这样写好吗?我以为对那些仍相信小说认识、认知意义的读者是很珍稀的,他因此更抓得住常常是隐藏的、或至少难以确认的思维线索,得到了亲切的引领如但丁如此感激维吉尔的带路和解说,知道怎么正确的、或说放心(放心带来专注)的读和想;但对于奉命为这部新小说写篇文章的人则显然不太好,不知道该怎么切断话题的绵延不绝,回溯不了恰当的起点,说昆德拉的这一本书,却不断变成说他一生的全部书写和思维。 哲学家阿甘本用一整本书(《剩余的时间》),来谈《圣经·罗马人书》这篇使徒保罗陷入最深沉思、几乎是往后千年哲学思维起点(奥古斯丁、康德……)的文献,他只讨论了第一句: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看来,我们一篇短文大概只允许来说前五个字:庆祝无意义,还只能省略地、无端地来讲。武断是语言文字的局限使然,不是我的原意。 昆德拉在巴黎花神咖啡馆前, 年7月3日,米兰·昆德拉(中)与法国作家让-皮埃尔·费伊(左)等人参加密特朗总统专门为文化人士举办的活动。这一年,昆德拉拿到了总统亲笔签署的公文,正式成为法国公民昆德拉, 米兰·昆德拉写作的四个原则 小说关于历史能说出什么特别的呢?或者说:您处理历史的方式是什么? 昆德拉:以下是我的几个原则。首先:所有的历史背景都以最大限度的简约来处理。我对待历史的态度,就像是一位美工用几件情节上必不可少的物件来布置一个抽象的舞台。 第二个原则:在历史背景中,我只采用那些为我的人物营造出一个能显示出他们的存在处境的背景。比如:在《玩笑》中,路德维克看到他所有的朋友与同事都举起手来,轻而易举地表决赞成将他开除出学校,从而彻底地改变他的生活。他确信,如果需要,他们也会同样轻而易举地表决赞成将他处以绞刑。于是他对人的定义就是:一个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将他的邻人推向死亡的生灵。路德维克这种根本性的人类学体验因此是有一些历史根源的,但对历史本身的描写(D的作用,恐怖的政治根源,社会机构的组织,等等)并不让我感兴趣,您在小说中找不到这些东西。 第三个原则:历史记录写的是社会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所以我的小说讲的那些历史事件经常是被历史记录所遗忘了的。比如,在一九六八年捷克斯洛伐克被俄国入qin占领之后几年内,在对民众施行高压恐bu之前,官方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灭狗行动。这一历史片断被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完全忘却了,而且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但它具有极高的人类学意义!我仅仅通过这一历史片断就暗示出了《告别圆舞曲》的历史氛围。 另举一个例子:在《生活在别处》的决定性时刻,历史以一条不雅观、难看的短裤的形式介入,在当时找不出一条同样的短裤来:雅罗米尔面对着他一生中最美好的情色机会,由于害怕被看到穿着短裤而显得可笑,不敢脱衣服而选择了逃跑。不雅观!这也是一个被遗忘了的历史背景,但对一个被迫生活在极q体制下的人来说,是多么重要。 但最深入的是第四个原则:不光历史背景必须为一个小说人物创造出新的存在处境,而且历史本身必须作为存在处境来理解,来分析。比如: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杜布切克被俄j队逮bu,绑架、关入j狱、威胁,迫不得已跟勃l日n夫交涉之后,回到了布拉格。他在广播上讲话,可他说不出话来,他喘着气,在话与话之间作出长长的、令人难以忍受的停顿。这一历史片断(其实这一片断完全被人遗忘了,因为在两个小时之后,广播电台的技术人员被迫剪掉了他讲话中那些艰难的停顿)向我表明的就是软弱,作为存在的一个非常普遍的范畴的软弱:“面对强力,人总是软弱的,即使拥有杜布切克那样健壮的身体。” 特蕾莎无法忍受这一软弱的场面,它让她厌恶,让她感到羞耻,于是她更愿意侨居他乡。但面对托马斯的不忠,她就像是杜布切克面对勃l日n夫:手无寸铁、软弱不堪。而您已经知道了什么是眩晕:就是沉醉于自身的软弱,是无法遏止的坠落的欲望。特蕾莎突然间明白了“她属于那些弱者,属于弱者的阵营,属于弱者的国家。她应该忠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是弱者,因为他们弱得说话都透不过气来”。沉醉于软弱中的她离开托马斯,回到了布拉格,那个“弱者的城市”。历史环境在这里并非一个各种人类处境在它前面展开的背景,而是本身就构成一个人类处境,一个扩大化的存在处境。 同样,布拉格之c在《笑忘录》中,不是以它的政治、历史、社会范畴,而是作为根本的存在处境之一来描绘的。人(一代人)在行动(进行一场革命),但他的行动让他无法把握,不再服从他,于是他竭尽全力去弥补,想控制住这一不再听话的行动(一代人发起了一场对立的、改革的运动)而终究无济于事。行动一旦失控,永远无法弥补。 米兰·昆德拉8本书的开头与结尾1.《玩笑》 开头:哦,到了,多年以后,我又重返故里。结尾:我们围着他站了约十分钟,这时第二小提琴手回来了,做手势要我们把他扶起来,从胳膊下架住他,我们扶着他穿过那群酒醉喧闹的年轻人,来到街上,一辆亮着前灯的白色救护车已等在那里。见之不忘的语句:受到乌托邦声音的诱惑,他们拼命的挤进天堂的大门,但当大门在身后砰然关上时,他们发现自己是在地狱里。一切都终将被遗忘,同时又无论什么事情都无法挽回。挽回的作用(或通过报仇雪恨,或宽宥原谅)必须有遗忘为基础。任何人都无力挽回已铸就的过失,但一切过失却都将被遗忘。 2.《笑忘录》 开头:现在是一九七一年。结尾:那男人说着,他们饶有兴趣地听着,而他们裸露的性器官这时正傻呆呆地忧伤地看着地面的黄沙。 3.《生活在别处》 开头:究竟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怀上诗人的?结尾:他望着水里他自己的脸。突然他看见巨大的恐怖从那张脸上掠过。这些东西就是他最后见到的。见之不忘的语句:所谓美,就是星光一闪的瞬间,两个不同的时代跨越岁月的距离突然相遇。美是编年的废除,是对时间的对抗。这是一个流行离开的世界,但是我们都不擅长告别。最糟糕的不在于这个世界不够自由,而是在于人类已经忘记自由。我们选择了这个方法正如你选择了你的命运,你我的选择都同样是不可改变的。然而,每一个人都遗憾他不能过其他的生活。你也会想过一过你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你所有可能的生活。只有当一个人上了年纪,他才可能对身边的人,对公众,对未来无所顾忌。他只和即将来临的死神朝夕相伴,而死神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他用不着讨好死神;他可以说他喜欢说的东西,做他喜欢做的事。 4.《不朽》 开头:这位太太大概六十岁,或者六十五岁。我平躺在一把朝着游泳池的躺椅上望着她。 结尾:汽车的喇叭响个不停,我听见愤怒的人群在大叫大嚷。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阿格尼斯渴望买上一枝勿忘我,只要一枝;她希望把花举放在自己的眼前,作为美的最后的不为人所见的象征。见之不忘的语句:没有一点儿疯狂,生活就不值得过。听凭内心的呼声的引导吧,为什么要把我们的每一个行动像一块饼似的在理智的煎锅上翻来覆去地煎呢? .《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开头:尼采常常与众哲学家们纠缠一个神秘的“永劫复归”观:回味我们生活中曾发生的事吧,一旦它们日复一日地重演,甚而永无休止地重复重演本身,!如何阐释这种近乎癫狂的幻念? 结尾:钢琴和小提琴的旋律幽幽地,从楼下丝丝缕缕地飘下,再淡淡地消灭在夜空里,远去无痕。见之不忘的语句:令她反感的,远不是世界的丑陋,而是这个世界所戴的漂亮面具。表面是清晰明了的谎言,背后却是晦涩难懂的真相。压倒她的不是重,而是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人一旦迷醉于自身的软弱之中。便会以为软弱下去,会在众人的目光下倒在街头,倒在地上,倒在比地面更低的地方。 .《慢》 开头:速度是出神的形式,这是技术革命送给人的礼物。 结尾:马车消失在雾中,我发动了车子。见之不忘的语句:缓慢的程度与记忆的浓淡成正比,速度的高低与遗忘的快慢程度成正比。乐趣不论平凡还是不平凡,只属于感觉到的人。 7.《无知》 开头:“你还在这干什么?”她说话并不凶,但也不客气。 结尾:他透过舷窗,看见天空深处有一圈低矮的木栅栏,在一座砖房前,一棵细高的冷杉,像一只举着的手臂。见之不忘的语句:孤独:独自穿越生命而不用任何人关心;说话不用人倾听;经受痛苦而不用人怜悯。生活,生活中没有幸福。生活就是:扛着痛苦的"我"穿行世间。而存在,存在即幸福。存在就是:变成一口井,一个石槽,宇宙万物像温暖的雨水,倾落其中。逝去的时光愈是辽阔,唤人回归的声音就愈难抗拒。这样的说法似乎言之成理,但却不是真的。人不断老去,生命的终局迫近,每一瞬间都变成愈来愈珍贵,根本没有时间可以拿来浪费在往事上头。我们必须去理解这个关于乡愁的数学悖论。 8.《告别圆舞曲》 开头:秋天到了,树叶开始变色,发黄,发红,发褐;位于美丽山谷中的小小温泉城,仿佛被一场大火围住。 结尾:伯特莱夫说着挎住妻子的胳膊,然后在月台柱灯的照耀下,他们四个人一起走出火车站。见之不忘的语句: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嫉妒那样消耗一个人的全部精力。独特的人,当他们成功地让别人尊重他们的独特性时,会有一种相当漂亮的人生。你们让所有的人成为凶手,而且,这样一来,你们自己的屠杀罪就不再是一桩罪行,只不过成了人类一个恶不可避免的特征。 《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 雅众文化 南京大学出版社/-2 ·他不仅是误解的受害者,也是误解的制造者。 昆德拉说:“我出生于4月1日。这在形而上层面并非毫无影响。”昆德拉的写作人生,像是上帝与他开的一个玩笑,充满了误解:他不仅是误解的受害者,也是误解的制造者。这源于特殊的历史境遇,也源于他对媚俗的反抗和对文学的独立性的追求。 他曾先后两次被开除出dang,因立场问题遭受谴责;而后离开捷克,移居法国,用法语写作,于捷克人,这是背叛,于自身,则切断了文化的根脉。在特殊时期,他的捷克语作品在捷克斯洛伐克遭禁,但在天e绒革命之后,他仍没有迎合政治环境的变化,也不顾出版商和读者的要求,拒绝在国内出版其捷克语作品。他不认同年后,捷克人对传统的彻底唾弃,更不想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政治的注脚。 在《被背叛的遗嘱》里,他说:“我深深渴望的唯一东西就是清醒、觉悟的目光……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实践某一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 通过小说,昆德拉勘察人的存在状况,拓展人的存在的可能性,他希望作品随时间的推移,仍闪现出具有内在统一性和普遍性的艺术之光。 外界对于昆德拉的误解也因为他很少对公众谈论自己,也很少留下与文学文本无关的材料,写作他的传记难度可想而知。布里埃的这本传记以昆德拉的理论性随笔与文学文本为基础,将他个人的艺术、文学、政治与精神历程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同时借助与昆德拉有直接交往的作家、翻译家、评论家提供的一些公开的和迄今尚未发表的资料与交谈内容,为读者展示了被误读的作家昆德拉的一生,以及他的精神世界。 悲剧与喜剧[法]让-多米尼克·布里埃刘云虹、许钧译在恐怖中,我明白了幽默的价值。那时我二十岁。我总能从微笑的方式中辨认出谁不是斯d林派的人,谁是我丝毫不用害怕的人。幽默感是一种可以信赖的辨识的特征。而自那以后,我被一个失去幽默的世界吓坏了。——昆德拉临近20世纪0年代,最初几篇短篇小说的写作让昆德拉明白,从此以后自己将成为小说家。的确,直到那时他只写了一些短的文本,但自那时起他力图写出篇幅更长的作品。他必须找到一个能在长度上“支撑到底”的主题。年,他来到俄斯特拉发,那是20世纪0年代初他流亡时待过的矿城。在那里,朋友们向他讲述了一个奇怪的故事:一个年轻女工因为偷墓地里的花送给自己的情人而被逮捕。他写道:“她的形象始终没有离开我,我的眼前浮现出一个年轻女人的命运,对她而言,爱情与肉体是相互分离的世界。”同时,或许因为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他想象了一种情色行为,它的基础不是爱,而是恨。最后,对“国王巡游”的模糊记忆又在他脑海中出现,从孩提时代起,这个摩拉维亚的民间仪式就令他着迷。正是从这些散乱的景象出发,他着手构建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玩笑》(?ert,)电影剧照《玩笑》的情节在两个不同时期展开:第一个是年,布拉格z变结束后不久;第二个是十五年之后,并不确切,小说开头仅有只言片语写道:“就这样,多年以后,我又回到了家。”在对第一时期的描绘中,昆德拉细致入微地展现了捷共掌权的过程,以及实行检举和镇ya制度所带来的热情,这样的描写方式使《玩笑》被列入政治书籍一类,也让它的作者出现在持不同z见作家的行列。正如他9年所解释的那样,这两点都违背了事实:“这是一部探讨人类价值脆弱性的小说,而不是一部想揭露某种政治制度的小说。小说家的抱负要略大于瞄准某种短暂的政治制度。”在“布拉格之c”的影响下,对《玩笑》的这一错误认识又被强化,直到8/9年的“天e绒g命”及捷克政q再次变更,昆德拉的小说才最终摆脱政治小说的标签。此前,他竭尽全力试图消除误解。19年,当该书在捷克和法国都还未出版时,他便赶在前面,解释了自己采用的方法:“在我的《玩笑》中……20世纪0年代吸引着我,因为那时,历史带给人们从未有过的经历,并以无法重复的境遇和意想不到的角度表明了这一点,突然,它丰富了我关于人类及其处境的疑惑和观念。”十三年后,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他认为有必要再次明确自己的意图:“我所感兴趣的,不是历史描写,而是形而上的、存在的和人类学的问题……总之,就是由某种具体历史境况的聚光灯所照亮的所谓永恒人类。”在昆德拉看来,斯d林时期本应揭露出人类经验的诸多新方面。小说家把这种专制与其他专制区分开来。他着重强调了它在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设立的具有悖论性的差异。“合乎规定的艺术流派是现实主义。然而,它可能与现实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流行的是对青春的崇拜。可我们一切真正的青春都被剥夺了……被当众宣布的只有欢乐,我们却丝毫不敢开玩笑。”从这种对悖论的经验中,昆德拉得出不少教训。正是这一经验让他拒绝谎言并由此形成他的反抒情态度,也让他认为必须破除神秘化,这决定了他对于某些小说主题的选择,尤其在《告别圆舞曲》中:“当今天我听到人们谈论孩子的天真、母爱的无私,谈论繁殖后代的道德责任、初恋的美好时,我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我已经上过课了。”*《玩笑》是年开始创作,19年12月完成的。当时,手稿被送到审c委员会,留存了一年后才被批准原封不动地出版。表面来看,这一处理很温和,但昆德拉认为应将其重新置于时代之中:“在20世纪0年代,早在布拉格之c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其整个意识形态已经死气沉沉,只是装装门面而已,任何人都不把它们当回事。”此外,该书谈论的是“过去”时代的暴行,如果它涉及当前形势,那么就会有更大的被查jin的风险。MilanKunderaen,photo:GisèleFreund,IMEC/FondsMCC,GaleriedelavilledePrague年春,《玩笑》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同时出版的还有另外两部批判斯d林主义的小说——捷克人路德维克·瓦楚里克的《斧头》和斯洛伐克人拉迪斯拉夫·姆尼亚奇科的《权力的滋味》。《玩笑》一出版,人们便竞相阅读:几个月内销售了十一万七千册,对一个人口不足一千五百万的国家而言,这个数字相当可观。作者年回忆道:“当时我三十八岁,默默无闻。我惊愕地看到,这三部书都是三天内就销售一空。”无论如何,这个想法令人吃惊,要知道,年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是非常有名的作家,年和19年出版的《好笑的爱》前两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书刚出版,拥护者安东宁·J.利姆便竭力让国外也知晓此书,首先是法国:“年,人们的旅行已经不受限制。我把书装在口袋里,在巴黎把它交给了我的朋友阿拉贡。他不懂捷克语,但我向他解释说《玩笑》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他相信了我。在他的安排下,我们与克洛德·伽利玛共进晚餐。我向他们概述了书的内容,他们十分信服。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昆德拉将成为世界文学中的重要作家。他始终是位与众不同的作家。而且,书写得非常棒。他的捷克语令人赞叹。这门语言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并非如此。他的特征是反讽。他是位讽刺作家,属于哈谢克、恰佩克,甚至卡夫卡的传统。这非常捷克化。这些作家都擅长反讽,但各不相同。任何伟大的文学都是部分反讽性的。”考虑到将书译为法语所需的时间,《玩笑》计划于年9月在法国出版,商定由阿拉贡撰写序言。然而,8月份,华沙条约组织的j队r侵捷克斯洛伐克。阿拉贡被迫在最后时刻修改文章,以便根据各种事件来阐明小说。小说在朝夕之间便声名鹊起,代价却是对作者意图的违背。昆德拉就误解进行了如下解释:“(在捷克斯洛伐克,)文学批评不太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fz/9546.html
- 上一篇文章: 静,有一种无以伦比的美
- 下一篇文章: R第期米莱斯2英国拉斐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