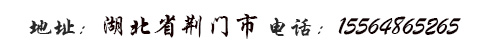雪绒花文学付继玲父亲
|
治疗白癜风最好的中药 http://m.39.net/pf/a_4790113.html父亲文/付继玲 记忆中母亲身体一直不太好,加上性格内向,所以不咋爱出街。就这,我的童年便和父亲捆绑在一起。田间地头,农闲街头,叔婶炕头,父亲的怀前背后总少不了一个留着短发,小脸蛋裂的像沙皮山药蛋一样的小女孩。 父亲三十六岁得的我,所以也是如获至宝,按说带孩子这种琐碎之事一个大男人日子久了会烦,可父亲半点不显,别人一句“付选又哄闺女了,看看小闺女这眼神机灵的”,父亲总是憨憨地一笑,嘴角向一边咧着。就这样年复一年的,父亲笑着,我乐着。 童年的日子总是轻飘飘地来,又轻飘飘地去,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光都充满了新奇和快乐。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子方圆十几里没有一段像样的路,堡子里人们的日常耕作都是人背驴驮,这就更增加了农活的繁重。记忆中父亲叔伯他们每年刚过大年初六就开始送粪了,那时几乎家家户户都养几只羊,这羊粪就是一年庄稼的肥料。年节刚过完,北方的天还是很冷的,羊粪还在圈里死塌塌的冻着,父亲便用镐一镐一镐的生刨,到下午被刨起的粪块见着太阳有了些许松动,父亲再用榔头把它们溜烂,每天重复着,直到一圈粪都被父亲侍弄成碎块块,父亲便叫来和他搭伴种田的叔叔(有好多农活是一家人不能独立完成的,还有就是那时候家家穷,只能养起一头毛驴,所以搭伴我们那叫搁具就是一种必要的耕种形式)一起把粪装进一条长长的毛口袋里,然后父亲用他那双迸满青筋满是老茧的大手紧紧抱住口袋上半面,叔叔则抓住底部用力一端(我们那叫打垴),粪口袋一下落在父亲肩膀上,然后父亲再用力往驴背上一掷。怀了驴驹或是老点的驴只能驮一口袋冻粪,可想而知,这一口袋粪有多重,所以记忆中总少不了母亲隔三差五的唠叨“就你窍,天天抱口袋,咋不和他们叔轮着抱”父亲淡淡的回一句“他叔不是身体不好蛮,咱省下那劲在哪里。” 粪就是这样一回三口袋,三口袋地被父亲他们一趟一趟地沿着蜿蜒的山路送到地里,自然我也在这路上一趟一趟地留下了歪歪扭扭的小脚印。赶上路稍微平坦一点,父亲便将我抱起来放在驴背上,我两只小手紧紧扒住粪口袋。心里那叫一个美。每当这时,父亲总是会摸摸驴头,现在才懂他那时是心疼自己饲养的驴又因驮上我而加重了苦力。 阳坡弯那浅浅的绿在默默渲染着春的生机,沉睡的大地开始慢慢苏了。南梁,东梁,南湾视线所及之处都是春耕的父辈们。父亲用僵绳把两只驴头拴在一起,然后又拿两副绳线将驴各自拦在中间,用一个铁勾将绳线和铁犁勾在一起,父亲在后面一只手扶着犁柄,另一只手拿着鞭子。沿着墒沟一趟一趟来回往返。铁犁前面那个滚动的圆轮子不停的发出吱纽吱纽清脆的响声,伴随着偶尔的鸟叫声,是那个季节最美的音乐。快到中午时分,父亲停下犁,换上一种叫磨的农具,要将上午犁好的地磨平,一是怕风干了水分,二是便于耕种,每当这时也是我最期待的时刻。其实一上午早不知道问了父亲多少回了“爹多火耱地了?”“快了,你又想爬耱悠了昂”。父亲让我爬在耱中间,然后又到地边找来两块比较大一点的石头,一边一块(因我太轻,压不住磨),这就齐活了。父亲一扬鞭子,我便有一种飞的感觉,鼻子里泥土的清香,耳边呼呼的风声,鸟叫声……几趟来回地耱完了,我蹦哒着下了磨,父亲的嘴又向一边咧着,这次他是笑眼前这个满身,满头,满脸的黄土女儿。 远处的山绿了,那一弯弯梯田也绿了,它们遥相呼应欢快地连成一片。父亲光着黝黑通红的膀子,挽着裤腿,光着脚丫锄着田里的杂草。任由汗水亲吻着土地。锄地这活老躬着腰这一个姿势,时间久了腰疼,别的叔伯累了就坐在地头起抽一锅子旱烟,解解乏,父亲一生不吃烟,不喝酒,腰疼了就带上我到地圪楞上,阴坡弯拔药材,这就算是歇歇了。金根茬(药用名柴胡)赶上地潮不用刨,用手轻轻一拔就起来了,马草(知母)的用俩齿的凿子刨,父亲性子急,干啥也快,找对地方一会功夫一大堆黄澄澄的药材就刨好了。每回这一堆药材里都少不了我的美味(野菜),什么麻奶奶,臭椿,布布英(实在对不上通用名)。有时难得父亲坐在地头上歇一回,我就扒着他通红的膀子,无聊的撕扯着他那被太阳炙烤的一大块一大块的肉皮。“爹疼不”“不疼,哎呀长大了还懂问爹疼不了,”父亲手向后一掏,将我揽在怀里,两只粗糙的大手轻轻的搓着我的脸,父亲笑着,我乐着。 黄澄澄的谷穗垂着沉甸甸的穗头,放眼望去,到处一片令人心醉的金色。田野里男女老少个个挥舞着镰刀,阵阵笑声飘洒着丰收的喜悦。那弯弯曲曲的山路上穿梭着赶着驮满丰收的毛驴的父辈们,不同于别的叔伯的时父亲背上总是还要再背上一大背庄稼。我却是驴背谷垛上的宠儿。打谷场上,谷屯里,都见证了父亲的笑,那微微的一咧。 吃过早饭,按部就班的随父亲到担水沟饮驴。北方的冬天,那风硬的真好像是刀割,父亲一手挑着水桶,一只手攥着我的小手,我攥着驴僵绳。下沟的路是一道弯弯曲曲的陡坡,呼呼的风声伴着咯吱咯吱的脚步声。天天如此,却少不了父亲心疼的埋怨声“这么冷,不叫你跟非得跟,冷不冷““不冷”我一边蹦哒,一边赶紧回答,生怕下回不让跟。说来也怪,那年头孩子们也结实,一年到头不咋生病。快乐的时光总是不知不觉,一会功夫一担清凉凉的泉水挑到家中。母亲赶紧抱起早以冻的小脸蛋通红的我,往炕头上一放,嘴里叨叨着和父亲同样的话“不叫你跟,非得跟,冷不冷,”我哪管她说啥了,早自顾自地玩我的羊谷头子去了。父亲吧水倒进大缸里,把桶挂在院里的两叉木桩上,又清了驴槽,一番忙活进家斜跨在炕沿边上,两只手向后一伸,我立刻扑向他那宽厚结实的背膀上,这也许就是天长日久的默契。“窜门了,”父亲边走边叨叨着,“去大爷家的叫大爷大娘了”,“嗯”,我在父亲背上扑腾着小脚板。 日子就这样轻飘飘的过着,我和父亲就这样他笑着,我乐着。 有一天,日子在我还不懂啥叫沉重的时候变的不再轻飘,那年我十一岁。 喀,喀喀一阵急促的干咳将沉睡中的我惊醒,睡眼朦胧中看见父亲爬在炕沿外,地上一大滩鲜红的血。生平第一次感到钻心刺骨的怕。母亲一手端着一碗热水,另一只手拿着手巾,脸色苍白的说,“我给叫他四爷去北山岭叫李秀忠去!”父亲也许是看见自己吐了这么多血,也有点感觉不对,勉强点了点头,换成往日,父亲是不会同意请医生的。母亲赶紧冲向了漆黑的夜。一会,李秀忠挎着药箱子急匆匆的进了家,四爷也喘着粗气跟在后面。把脉和询问过后,李秀忠拿出一个小铝盒,取出打针管子,让母亲烧了一暖壶热水,洗净针管,给父亲打了一针,然后又拿出一团胶管让母亲在锅里蒸了几分钟,取出来又给父亲输上液。“付选今咱先输点液止止血,明天叫我说你不如到西合营检查一下,看看是啥病,哪里的血,毕竟单靠把脉怕吃不准病,别再耽搁了”,“没事哇按说,估计是感冒咳嗽引起的,震的血管破了,咱先治的紧看的紧,要不不显轻再说,你明还过来给我输上”。“那可轴的了,你明还来给他输吧,去医院怕花钱,”四爷一边附和着,“昂”,李秀忠无奈地应合。 几天后父亲尽然“好了”。咳嗽少了,痰里也没血了,田间地头又成了他的舞台 没过几天,又咳,用药又止,医院看看,终是拗不过父亲的执拗。 父亲身体每况愈下,原来浑厚的背膀也单薄了很多,圆润的脸盘明显瘦了一圈。 那一条条崎岖不平的小路上,那一块块寄希望于生存的田野里,依然有他熟悉的身影,只是比往日疲惫,拖沓了许多。 父亲就在轻一天重一天的四五个月后的一个傍晚再一次病倒。这一次是肚疼,一向瓷实的父亲竟然啊呀啊呀的叫着,两只手用尽全力的按着肚子,额头上的汗点子不停的滴嗒。炕头,后炕来回地挪动,坐不是,跪不是。再次请来医生,另一边二爷和四爷商量着“不行把孩子大爷叫来吧,咱医院吧,”当家子大爷的儿子被喊去三十里外的村子叫大爷。大爷连劝带逼地说通了父亲。 母亲从双开门小红柜里取出一个布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用麻纸和线绳捆的紧紧的,鼓鼓的小包包,递给大爷,大爷随手打开,里面十元的,五元的,五毛二毛的大爷数的数一共.3块,大爷又从自己兜里掏出准备好的二百撂在一块,二爷四爷爷各自回家取来钱一并交给大爷,当家叔婶这家五十,那家三十“明咱先拿这九百去医疗看看啥情况。”“昂,先看看到底啥病,快一年呀付选这身体一直闹病”,大爷四爷他们谈论着。 肺结核,严重十二指肠溃疡,得住院治疗。 半个月后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下午放学回家惯例性的约好四百去地拔兔草。刚一进院,就看见父亲蹲在菜畦里拔杂草“爹,”飞似的扑向父亲,父亲站起来紧紧的把我搂在怀前,两只手轻轻的搓着我的脸,只是少了往日的粗糙。父亲红着眼圈,始终没让眼泪流出来。因为这一次是我和父亲分开最长的时间。父亲急切的领着我进了家,从炕头的布兜子里取出半袋动物饼干“看这啥”“饼干”,我尖叫着,瞬间又赶紧掩饰住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以长成大小孩子了,模模糊糊地懂的父亲生病了这些好吃的要留给他吃,如果父亲看我吃的香就更舍不得吃了“爹你看这块是兔子这块是……”,“老三走吧,”爹我和四伯拔兔草去”,“去吧,长大了会给干活了。” 出院后的日子里,父亲就没离开过药,吃的药片片,打的针剂。当然更没有离开过他的土地,尽管这样,父亲那么深爱的土地就像在欺负一个瘦弱,疲惫的病人,那草就像打了营养液似的疯长,父亲吃力的拎着锄头,几乎没有还手的能力,剩下的只是那一声声长吁后的哀叹。 六七月的天,雨说来就来,几声闷雷刚过,铜钱大的雨点子就来了。一路狂奔放学回家。“娘,俺爹还没回来了?”“没了蛮,这雨一会也不欠。我掉头跑到大南场,想着看看有没有父亲的影子。南山头朦胧如烟,灰濛濛一片。突然拐弯处一个影子朝这边走来,风搅雨愈加历害,色皮带叠的雨皮被风吹的一阵一阵要飞,雨水顺着帽尖直往脸上流,湿漉漉的手不停的擦着眼,是,是父亲骑着驴的影子。俺爹今骑驴?一种新鲜还是奇怪的念头一闪而过。因为父亲从来舍不得骑他的驴。 就在这天晚上,父亲又一次肚疼的厉害。 “医院看看吧,付选!”四爷说,“那可不行四叔,把羊卖了她娘们咋过了,孩子还要念书,外边还借了那么多饥荒,万一我有个啥也好把羊卖了还人家,医院也住了,吃药打针也没短,随它去吧。”母亲悄悄扭过身子,家里一下子静的可怕。 隔三差五的肚疼,把父亲折磨的已经不成样子。记得父亲肚疼的厉害时,就拿来家里那根长擀面杖和一块小平木板,木板放在肚子上,用擀面杖一头顶着木板,一头和墙顶着,父亲半跪着熬过这一阵子,再厉害了父亲就躺在炕头上,把枕头放在肚子上,然后把一块有二三十斤重的石头压在枕头上,额头上密密麻麻的汗珠子不停的流,父亲有气无力的呻吟着。每当这时我都是恐惧的蜷在后炕,不敢动一下。一向因苦重而饭量大的父亲对饭也索然无味,最爱吃的酸菜泡糕也不香了。偶尔勉强吃几口,不是吃完就肚疼,就是过后就吐了。母亲便从粟子瓮里摸出两个鸡蛋,抓一把稀缺的白面,倒几滴麻油,给父亲摊个鸡蛋饼,每次这时父亲都会重复一句话“一个就行了,攒着卖了给孩子买铅笔。”“给孩子掰块,我吃不了那么多”。母亲就象征性的给我掰一小块,“我不吃,”母亲冲我挤挤眼,我明白了她的意思,吃了油沓,父亲这才肯端起碗来。有一次姐姐不知道去哪里回来给父亲买了个午餐牛肉罐头,一个小板铁盒子,不知道咋吃,硬生生地用刀将盖子划开,挖出几块给父亲,“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了,”父亲边吃边说,“再给我挖几块,”母亲赶紧接过碗,全家人笑了,这好像是父亲病重后全家人第一次这么开心。以致后来每到副食店看到那个小板盒子都会不由的想起父亲。那盒午餐牛肉罐头和偶尔吃一次的鸡蛋饼就是父亲一生吃过的最奢侈的东西。 最病重的两个月里,父亲以经不能起炕了,每天躺在那双补丁落补丁的被子里,干瘪青黄的肉皮紧紧的贴着骨头。高高突起的颧骨,深深塌陷的眼窝,更显得一双眼睛大而无神。干巴苍白的嘴唇,微弱的呼吸着…… 父亲终是没熬过病痛的折磨,于年大年初一下午一点多带着牵挂永远地离开了我。 和父亲在一起的年头很短,故事很长…… 落笔之际,我愿这些关于父亲的文字能挺起一个农民父亲勤劳,善良,慈爱的风骨。笔下那些故事是父亲流动的血液,让他们在以后所有的日子里静静地流淌。 作者简介:付继玲,女,汉族,河北蔚县人,生于年,普通家庭妇女,性格开朗,待人真诚,爱好唱歌,喜欢文学,希望有更多的机会开阔视野,提升自己。 雪绒花原创文学专题: 雪绒花文学阅读感言 雪绒花文学同题诗会专辑(一) 雪绒花文学同题诗会专辑(二) 雪绒花原创季同题散文《冬日》征文作品 雪绒花原创文学作家推荐: 何凤山|周绍明|阳光牧场|张帅|刘建军|张东海|苏立敏|王树民|高玉琴|胡雨梵|赵合|张玉武 投稿要求:小说、散文限字内,优秀稿件可以适当放宽;诗歌要求一次投稿3-5首(或50行)以上;稿件必须原创首发,杜绝抄袭,文责自负。能提供与诗文内容相契合的配图者优先选用;文章请用word或wps文档,以正文+附件的形式发送;图片或照片请用JPG的格式单独以附件的形式发送,同时,请发字以内的作者简介及个人清晰生活照片一张。投稿请一律按要求格式发到投稿邮箱,同时请加主编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fl/8492.html
- 上一篇文章: 天津中宝制药诚招代理加盟
- 下一篇文章: 微型小说自寻短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