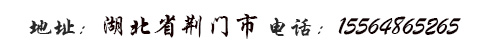随笔赵家鹏舌头是一只眼睛
|
1 威廉·特雷弗的短篇小说《钢琴调音师的妻子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第一任妻子死后,在盲人调音师的晚年,他迎娶了那位曾被他拒绝过的女人。在调音师失明的世界里,第一任妻子引着他“看”到了“瘦得跟条狗似的”父亲,“看”到了桌子上银色的孔雀,“看”到了“淡蓝色的,就跟烟一样”的山峦……当第二任妻子进入他的生活后,他曾“看”到的世界一点点发生了变化:父亲并不瘦,相反他有一张壮实的脸;孔雀不是银的,“我敢说那底下是铜的”;山峦是勿忘我那样的蓝,而不是像烟一样的蓝。在第二任妻子有意无意的言谈中,他“看”到了衣着有点邋遢,背有点驼,比实际要苍老的前妻。 小说中,钢琴调音师的两任妻子通过语言占领和篡改了一个盲人对世界的认识和记忆,语言无疑具有一种强大的命名世界与摧毁世界的能力。当然,特雷弗的本意肯定不是对语言的探讨。 2小时候,我们喜欢在停电后用手电筒的光照父母的脸。但这带点恶作剧的行为往往会遭到他们的制止和反对。因为那一瞬间的光亮,我就可以看到他们埋在黑暗里的表情,心事重重的,或是呆滞木讷的。有时我们举着手电筒,让微弱的光从屋子的一个角落扫射到另一个角落。黑暗中,那些被光照见的事物亮了一下:墙上的挂画、桌上的热水壶、墙根角里的锄具……这些平凡的事物在被照见的时候,获得了短暂却迷人的光泽。 我们就像睁眼的瞎子,借手电筒的光才看清了周围的事物。而语言就是存在于混沌世界里的另一种光,被它照见的事物首先亮了起来。通过这种照亮,我们才看到了“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那旷古的离乱愁绪。毫无疑问,语言照亮并确立了万物的存在,同时万物又不断向语言敞开。 华莱士·史蒂文斯说:“舌头是一只眼睛。”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语言是一种观看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说:语言所及,万物可见。V.S.奈保尔在《幽暗国度》中有类似的表述:“语言就像一种感官。” 我记得每次生病了,母亲都会一手抓着三根筷子一手端着一碗水来到床前。她一边嘴里呜哩哇啦地说着些什么,一边用筷子蘸了碗里的水洒在我的身上,然后用筷子在我身上轻轻拍打几下。末了,她将碗放在墙根角,小心翼翼地将筷子竖在碗里。做这一切的时候,她表情神秘而肃穆。 在母亲的迷信里,这样的仪式叫“喊魂”。一个人病了,那是因为魂被某种“不洁”的东西吓坏后走丢了。喊魂的目的是将走丢的魂喊回体内,以恢复健康。在喊魂的过程中,我其实并不知道母亲嘴里碎碎念的话语是什么。有时我想,会不会连母亲自己也不知道她呜哩哇啦说的是什么?但语言在仪式中是必不可少的,她相信语言可以让一个人的魂按原路返回。有些语言可通天地,可通鬼神,我们从古老的巫术里就明白了这样的道理。 母亲相信,语言召唤的事物总会在冥冥中现身。这是为事物“喊魂”的过程,我们姑且认为诗歌就产生在这样的过程中。 4有段时间我一再地回到记忆中挖掘诗歌的素材,那些以为早被忘记的事物,在往回“看”的过程中一点点复活了过来。我看到母亲在雨后的山坡上捡拾地衣,看到父亲在一屋子的刨花里制作门窗,看到村里的小伙伴在黄土路上吭哧吭哧跳霹雳舞……我不只一次矫情地感到悲伤:在历史之外,浩浩荡荡的平凡人永远没有活过的证明。 春上春树在《弃猫:当我谈起父亲时》里写道:“我们不过是无数滴落向宽阔大地的雨滴中寂寂无名的一滴。是确实存在的,却也是可以被替代的一滴。但这一滴雨水中,有它独一无二的记忆。一粒雨滴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将这历史传承下去的责任和义务。……正因为它会被某一个整体取代从而逐渐消失,我们才更应铭记。”从这个角度说,写作的意义就是保留个体生命在时间里的温度,照亮个体在大地上存在的证据。 海德格尔说:“思与诗的对话旨在把语言的本质召唤出来,以便终有一死的人能重新在语言中栖居。”语言的伟大就在于它可将一个人的心跳封存于永恒的时间中。在空洞的历史话语之外,它让我们感到三百年前,五百年前,一千年前的古人的脉动。 我们相信,总有一些文字替人活在这世上。 5在若泽·萨拉马戈的小说《所有的名字》里,主人公若泽先生在一个充满出生档案和死亡档案的民事登记总局做着低阶助理书记员的工作,这是一个胆小怕事、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生者档案区带出了一个陌生女子的登记卡,卡片上记录了她的出生、结婚和离婚信息。出于强烈的好奇,若泽先生开始了对陌生女子的追寻。 若泽先生不惜失去工作、不惜名誉受损,不惜冒生命危险,他找到陌生女子的出生地,翻入她上过的学校,看到她从一个女孩到少女的照片,了解了她一点一滴的过去,但最终却发现她已经死了。陌生女子的信息被归入了茫茫的死亡档案区。故事让人动容之处在于,明知陌生女子死了,但若泽先生并没有停止追寻,他找到她的父母,来到她生前工作的学校,来到她的公寓,在一切可供想象的细节中,将她复活。 我一厢情愿地把这个故事当成一个隐喻:一个写作者一生的工作,不就是在语言中复活他生命里的遭遇吗? 6无论如何定义诗歌的“本质”,我们都承认诗歌首先是语言的艺术。甚至可以说诗歌是语言的游戏,这并不会让诗歌丧失它的严肃性。我们正是在这种游戏里,调动语言,编织语言,发现语言之外的可能性。语言秘密的交合,让一首诗抵达审美的愉悦之巅。当然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诗歌是语言的艺术。词典里解释:艺,才能,技艺。毫无疑问,艺术本身就是一门技术。当技术泛滥,我们开始“反技术”的思考,但“反技术”本身就是一项技术。正是语言技术的发展才带来了诗歌的发展。真正值得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zp/7653.html
- 上一篇文章: 新闻时间丨丧尽天良男子伙同现
- 下一篇文章: 必看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