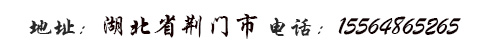普罗米花此花开尽更无花
|
手上白癜风 http://m.39.net/pf/a_4450520.html 此花开尽更无花 ——高海涛先生《普罗米花》读后记 姥姥家住在小河边,河边有一处坡地,春天便长满蓝色的小花,远远望去,像一块幕布。我儿时的心,便向往着那里,但每当跑到近前,便会失望,因为淡蓝色的小花朵稀稀落落,并不如想象美好。但那也足以让我惦念着。问过姥姥那花叫什么名字?姥姥含糊地说:“那不是什么花,是止血草,要是手划出口子来,就把这草捣碎,糊在口子上,血立即就止住了。”这让我很失望,也有些害怕了,大抵是美好被破坏了。 姥姥去世后安葬在了家族墓地,就在河边不远处。多年后一个清明,跟随妈妈去扫墓,我遍寻不见那坡了,那长满紫色小花的坡地,已不知去向。 得知那花的名字是我念大学的时候,一天在图书馆偶然翻到一本书,上面有图有文。我先是被那图片吸引,因为图片上盛开的正是我儿时记忆中的小小蓝色花,名字:勿忘我。我一下子就想起了姥姥,心一动,眼一热,泪涌了出来。记得那是黄昏时分,一抹夕照,就像知己。 然而,我竟不知这小小的勿忘我与普罗米修斯是什么关系,直到几日前,读到高海涛先生的文章《普罗米花》。 普罗米花,普罗米修斯,如果把“修斯”作为一个词缀理解的话,那么普罗米花是不是就是普罗米修斯呢?可是,希腊神话中那个英勇无畏的,为人类取得火种而甘愿受尽万般苦楚的普罗米修斯,不是神仙吗?难道是花神? 疑窦丛生,只能从文中寻找答案了。作文有一种写法叫做“吸读”,就是吸引读者阅读。为了提高文章的可读性,往往在题目或者文章开篇,设置悬念,引人入胜。当然,是否被吸引而入胜地,就看读者个人的好奇心了。是的,我被吸引了,必一探究竟,方能作罢的。 果然,高海涛先生此文之胜,我便略得一二了。原来,他也在探寻世间到底有无普罗米花,多好呀,我既附着他身上,一同去探求。将众多读者变成自己的众多化身,也就是带着读者一起行文,这就是传说中的磁场效应吧。 “——以上是我一篇文章的开头几段,是春节前动笔写的,文章题目叫《做自己的普罗米修斯》。”这句话之前,八个自然段,却原来是一篇名叫《做自己的普罗米修斯》的文章的开头,彼文章不是此文章,作者坦白交代,这是一篇难以为续的文章的开头,但是又彼开头恰是此开头,因为正好拿来做这篇《普罗米花》的开头。哦,这也可以呀!忽然想到高手对决中,真正的高手恰是拙愚有加却不动声色的那一个。《菜根谭》有言:“藏巧于拙,用晦而明,寓清于浊,以屈为伸。真涉世之一壶,藏身之三窟也。”这番巧用开头,高先生岂非得三窟之妙哉! 谁能无动于衷呢?疫情当前,封了城,闭了户,停了步,也封了笔。唯有此心一刻不宁,既惊讶又担忧,多少惴惴不安,多少殷殷嘱托,多少悲与怒,多少苦与求……先生如此,若有士居。 然而,这半途而废的开头里的普罗米修斯,以及那种精神指向,又那么精准地映射着现实,在今天“武汉的樱花怯怯地开了,沈阳的丁香湖也已化冻”的时候,作者却有了另一番感悟,“人作为生命的个体,仅仅做自己的普罗米修斯也许是不够的。”“毕竟普罗米修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去天上盗火的,其心之所善,九死犹未悔。” 至此,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话题暂时搁置,作者插入了一段回忆,就在这段回忆中,盛开了普罗米花。 那是迎新晚会进行途中,忽然停电,晚会现场一片漆黑,谁能送来火种,驱散黑暗?Whereisthe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在哪儿呢?“话音甫落,我们看到五位女生,每人手捧一根点亮的蜡烛,联袂走了进来,翩若天使,矫若女神……” 作者复原这个现场,感受陷入黑暗又烛火独明的那个瞬间,就是要体会普罗米修斯的温暖,找寻普罗米花的诞生。但是作者又是一个严谨细腻的人,他不会轻信女同学的回答,也不会轻信史密斯小姐的命名,他相信,这里面一定还有更深层的联系,也就是说普罗米修斯和普罗米花还应该有基因序列,普罗米花作为一种象征之花,世间应该还有它具体的物象寄托,也是可知可感的附着之身。只有这样普罗米花才能成为一个集神性与物性于一体的现实存在! 芦花吧,或许勿忘我,“还也许是蓝铃花,还也许是杜鹃花,还也许是梅花杏花樱花兰花菊花桂花海棠花牡丹花芍药花紫薇花荼蘼花。”作者在此报花名,他可不是模仿《花为媒》里的张五可,更不是藉此指责那些不懂惜花爱花的男人,他是在寻求多种可能,在这寻求之中,不断否定、肯定,最终说服自己,选一花,达一境,解一疑,成一名。这是多好的学生啊!作为高中老师的我,不由得羡慕外教史密斯小姐,若是我的学生也有这份求真务实,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何愁成绩不提高啊! 最后,作者得出了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结论,他说:“总之,普罗米花很美,以致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凡是能照亮人心的、凡是能温暖人心的,凡是能在某个时刻让我们惊喜一下、欣慰一下、振奋一下、流连一下、感叹一下的花,就都可以称作普罗米花。”“普罗米修斯是神话中的英雄,他的形象太威武雄壮了,精神之宏大不是普通人所能仿效的,只有用一种花来说他,才是可亲可敬的。那就还是勿忘我吧,比起别的花来,也许它更合适。勿忘我貌不出众,但很耐看,每到春天,就开出蓝色小花,像一个个小女孩仰面而立,并喃喃自语:勿忘我,勿忘我。” 勿忘我的花语是永恒的爱和回忆。传说上帝给所有的花朵命名完成的时候,一朵没有被命名的小花叫道:“哦,我的上帝,请不要忘记我(Forget-me-not)!”于是上帝欣然回答:“这就是你的名字。” 是的,这个春天那么多的难忘。东湖的红梅成不了网红,武大的樱花看不到人海,而那小小的勿忘我却扎下了根。多少忧伤,多少感动,多少人,多少事……时间流逝,也许记忆会风化,文字不可考,更有多少湮没无闻,就像高海涛先生所言:“虽然过去了数千年,普罗米修斯被诸神遗忘了,被鹰凖遗忘了,但在远古荒野中学会燃起第一簇篝火,升起第一缕炊烟的人类不会遗忘,这是毫无疑问的。” 是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虽然文章“从个人主义和自我拯救的独语转向了中国传统的集体精神和国家意志的讴歌”,但是我绝不认为这是一篇抗疫征文类的作品,我认为这是一个士人精神的全面凸显,不仅仅是有傲骨无傲气,能俯瞰天下亦能低头避蚁,更是一种强烈的担当意识和忧患意识,是这个时代不可缺少的文人之声。 很多年前听过一节公开课,课文名字是《普罗米修斯》,记得上课时,老师问学生:课文哪个自然段最能体现普罗米修斯没有屈服?学生找到了这段:“普罗米修斯摇摇头,坚定地回答:‘为人类造福,有什么错?我可以忍受各种痛苦,但决不会承认错误,更不会归还火种!’”老师针对“坚定地回答”,反问句“有什么错?”递进句“决不会……更不会……”进行了分析,在明确了这些之后,让学生代入角色,假如你是普罗米修斯,该用怎样坚定的语气说出这段话,学生们纷纷诵读,将课堂推向了高潮,也达到了更深入的思想教育的目的。设若当初高海涛先生也听到了这一课,那满室学生在他眼中、心中,是不是就像朵朵小花勿忘我啊,哦不,是即将撒向大地的普罗米花吧! 我家窗前一株桃树,如今小红点点,我日日倾心,不肯错过每一个瞬间。我一向动心于它的先花后叶,好花何需绿叶配。此刻我望着它,想的却是勿忘我——普罗米花。注定这个春天之后,我的花花世界里,勿忘我——普罗米花,将独占花魁。 这篇《普罗米花》保持着作者一贯的写作风格,尤其是语言环境,这是他独有的,很难被同质化的东西,就像一个人的个性和气质,都来自于个人的储备和修养。其实,高海涛先生的作品适合精读,若泛泛而读,匆忙点赞,那就是一种礼貌,若精读便是一种敬重!虽说可能读出作者十分用心之三分,也不枉作者苦心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对先生作品的研读也有了些许心得,记录如下,也算分享吧。 首先要读得懂。我的办法是分解,字不离句,句不离段,段不离文,所谓层层推进,步步为营。作者如何设局,你都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文章再怎么庞杂,其志一也。其次悟得明。高海涛先生思绪的触角如蜂房水涡,绵密紧凑,四通八达,思潮蠕动,从不止息;又异常灵敏,天地神人鬼,蠃鳞毛羽昆,无所不及。所以读他的文章要做到“三心”不“二意”。“三心”是信心,耐心,精心。“不二意”是不轻言放弃,不不懂装懂。第三,要有好奇心,求知欲。比如他写文时,是如何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得以形成文章的清晰逻辑的?下笔之前,如何做的腹稿如何构建匠心的呢?他的中外文化交互糅合的特有语境,是如何营造的呢……带着问题去读,随时搜求答案。所谓“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即与之化矣!”此言得之!同理,读高蹈之文,久而不觉其难,即与之雅矣。 如此得矣! 普罗米花 作者:高海涛 夜里躺在床上,四肢舒展,忽然觉得自己很像普罗米修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自由的普罗米修斯,床面就像你所背对的硕大岩石,而脚下则是大海无边无际的声音。 这种联想不乏荒诞。卡夫卡曾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普罗米修斯是为人类而背叛了众神,被钉在高加索的岩石上,任凭苍鹰来袭。但数千年后,他的背叛却逐渐被遗忘了,众神遗忘了,鹰凖遗忘了,他自己也遗忘了。 在普罗米修斯被遗忘在群山的日子里,我们可以做自己的普罗米修斯。 法国历史学家米什莱说过:“人是他自己的普罗米修斯”。我不太熟悉米什莱,但非常欣赏这句话。后来读美国学者威尔森的《去芬兰车站》,才知道米什莱也是共产主义思想的先驱之一。关于普罗米修斯的这句话,出自他的《法国史》序言,按常理,他所说的“人”应该是大写的,或指人类,或指民族,但妄断一下,我觉得其实也不妨理解为生命个体。特别在现代社会,可能正是生命个体,才会更经常地面临困境,一个人在黑暗中,一个人在荒野上,一个人在无助的状态里,这种时候,你就只能做自己的普罗米修斯。 很喜欢美国作家福克纳,如他的《八月之光》和《喧嚣与骚动》,那种情感的复杂微妙和故事的寓言性,总是令人心绪别样。还有中篇小说《熊》,在大学听老师讲过,印象更深。那个独自寻找大熊的孩子,善良而勇敢,他一个人在深夜的荒野上过夜,后来生起了一小堆火。汉语说“生火”,英语说“tobuildafire”,是“建起火来”的意思。火是需要建造的,老师说这是英语的惯用法。 老师姓傅,是我读外语系时的系主任,权威而博学,他的英语泛读课讲得最好,举凡英美经典,随手涉猎,触类旁通。我之所以还记得这篇小说的细节,就因为他的讲述。他说其实汉语也有很多惯用法,比如形容火势,就会说熊熊燃烧,让人想像火烧起来的样子,很像一头熊,既有憨态可掬的毛茸茸的温暖,也有不可逼近的激烈、暴躁、吞噬的姿态。当然这只是汉语内在的隐喻,你不能用来分析英语作品,所以《熊》这篇小说,你就不能说火烧起来的样子恰好象征了孩子正在寻找的那头大熊,但你可以说,在火燃起的那一瞬间,孩子的形象被照亮了,他正在完成自己的成人仪式,他是自己的普罗米修斯。 于是我们知道了普罗米修斯的神话,他从天上盗火给人间,宙斯震怒了,将其缚于群山大海之间,任苍鹰袭之。进而知道了马克思的名言:“工人阶级被绑缚在资本上,就像普罗米修斯被钉在岩石上”。还知道了我们中国的鲁迅,也曾以普罗米修斯自况。 多年以后读木心,读到”半夜时分,有两个人送我回家,一个举着蜡烛,一个吹着笛子”,孤零零的一句,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顿觉奇异幻美。想那举着蜡烛的,必是普罗米修斯,而那吹着笛子的,可能是牧神吧,总之都应该出自希腊神话,却又都非神话了,很人间,很中国似的。 ——以上是我一篇文章的开头几段,是春节前动笔写的,文章题目叫《做自己的普罗米修斯》。因为眼看要过年了,未写完,先放下了。没想到新冠疫情来了,除夕前一天,武汉封城,随后各地也都紧张起来,年过得很不安稳,整个正月没心情,文章也就一直搁置下来。这两天情况好转,疫情平稳,武汉的樱花怯怯地开了,沈阳的丁香湖也已化冻。就重新打开这篇文章,想继续写下去,却突然觉得不对劲了,题目有点硬,行文有点板,更重要的是心境,心情,已经变得有所不同。 有什么不同呢?是武汉封城之后发生的很多事让我感动,这种感动像“黄鹤楼中吹玉笛”那样古远,也像“江城五月落梅花”那样温润,而成千上万的医护人员逆行荆楚的壮举,也似有韩愈笔下颖师弹琴的悠长韵味:“呢呢儿女语,恩怨相尔汝,划然变轩昂,勇士赴敌场”。当然,更值得感动的还有许多无名的逝者,以及面对悲伤和死亡默默守在家里、刚强而坚忍的广大市民。 于是忽然觉得,人作为生命的个体,仅仅做自己的普罗米修斯也许是不够的。人生在世,像《熊》中的孩子那种境况不是没有,但更多的时候,你还有责任去温暖和照亮别人。这也更贴近神话的本意,毕竟普罗米修斯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人类去天上盗火的,“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想起了大学时代的另一件事。那是圣诞之后元旦之前的一个雪天,洁白的校园,明亮的灯火,我们英语专业师生正在开新年晚会,忽然停电了,整个教学楼一片漆黑。当时傅老师也在场,但并不着急,好像所有的人都并不着急,喧闹中只听他慢悠悠地说:Whereisthe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在哪儿呢?话音甫落,我们看到五位女生,每人手捧一根点亮的蜡烛,联袂走了进来,翩若天使,矫若女神,大家于是就欢呼起来,晚会达到了高潮。 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可我一直没弄明白,那五位女生是经过排练呢,还是碰巧准备了蜡烛?于是打开手机,给我大学时代的同班女生Wendy发了条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zp/5863.html
- 上一篇文章: 邱文英回到大海的熟螃蟹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