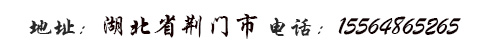ldquo白石门下rdquo的
|
“白石门下”的“胡家样”丁鼎 齐白石的成功,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画坛,对于近代画史,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齐白石的影响力对于这个时代,尤其是大写意的花鸟画是空前的。……今天,白石老人和他的一群嫡系传人、弟子、学生、已经相继远去。群星陨后,落英缤纷。他们所留下的作品,记录并诠释着每个人的艺术造诣、文化修养与创作历程。…… 斗转星移,随着时光的冲洗,我们越来越清晰地看清这些作品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同时,大浪淘沙,时间也将那些依附在艺术外的东西,毫不留情地过滤掉。剩下的才是相对静止的、具有研究状态的、或许能进入画史的那一部分。…… 时间是无情的,它又是公正的。因为公正,使我们相信有一个客观事实的绝对存在,尽管我们认知上的清晰度是相对的。好在时间又终归是有情的,它不管当时如何,到后来它一定会钟情那些真正好的艺术家,以及他们所留下的那些充满情致的艺术品。…… “家样”一词,是画史赋予那些具有巨大开创性画家的一顶桂冠。它首先是对其独立的创新面目、和有别于前人艺术形式的一种肯定。……中国画史上,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最早把北齐画家曹仲达所创立的“曹家样”,南朝画家张僧繇所创立的“张家样”,盛唐画家吴道子所创立的“吴家样”,晚唐画家周昉所创立的“周家样”并称为“四家样”。……尽管这里所说的“四家样”是专指佛教绘画的样式,但是,它是中国古代绘画史上,有关于以题材与风格为画派分类的雏形。开启了后世画家自辟蹊径,独树一帜的创作风尚。…… 通过对齐白石的学生胡翘然艺术的全面认识,本文以白石门下的“胡家样”为题,旨在以齐白石所开创的齐派,以及围绕齐派画家所形成的艺术理论与实践为基础。以出自齐门优秀而有代表性的画家为参照,从胡翘然绘画形式的主要特征与题材的丰富性上,论述胡翘然于齐白石的传承中,对现代花鸟画做出的特殊贡献,以及他晚年,在艺术创作与艺术探索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在这里,“家样”一词,可解释是自家的面目,或为自家的样式。不是创作粉本的底“样”。(齐白石在年轻做木匠的时候见到好的刻花就描下来,积累了许多花卉的样本,这些样本在他衰年变法的时候经过提炼加工最后成了“齐家样”)。…… “胡家样”,既是胡翘然自己的艺术面目,亦是他自己的艺术语言。它是由风格、章法、题材、书法、意境等中国画的多种元素构成。而这一切的完美组合,就表现出了胡翘然艺术上的一种系统性、综合性的总体特征,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胡家样”。…… 这种“胡家样”,大体由三大方面构成。 一曰:“胡家样”的风格。二曰:“胡家样”的章法。三曰:“胡家样”的题材。 总之,“胡家样”是胡翘然别具匠意,独出心裁,一种成熟的自家面目与艺术风貌。 “胡家样”的风格 论胡翘然绘画的风格,可以简单到只用四个字:“雅俗共赏”。也可以复杂到写一本书都不一定能讲清楚,它涉及到“随俗雅化”的问题。随俗雅化,是李斯在《谏逐客书》里提出来的观点,至少在两千多年来,没有人从美学的角度、或社会学的分析当中,来结合文化史发展中的一些现象给予必要的重视。…… 雅俗共赏,随俗雅化,是齐白石绘画晚年“变法”后的“定格”,也是后来齐派沿袭的画风。…… 讲不清楚的原因还是很多,因为形成风格的因素太复杂。古今中外关于风格的阐述也很多。但对于具体对象的研究,总是需对更多具体细节的探寻,而诸如此类地展开又并非易事。但理论上所谓的风格究竟是指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解释和界定,这首先需要知道何为风格。 在中国,风格在晋人葛洪《抱朴子》那里是指人的风度与品格。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则说是文章的风范与格局。尤其是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可谓是一部有关艺术风格的概论。其中对艺术风格有大块面的概括与划分,为后来的艺术创作,从理论上给予风格的确立与定位。…… 从唐代绘画理论开始,风格一词被用作对绘画艺术的品评用语,后来成为评论一词而广泛应用。所以历史赋予风格一词很多种意义,风格一词本身也包含了很多层意象。…… 风格对绘画,风格对于有着悠久文化思辨的中国画,并不是指一般艺术的特色、或仅仅是有别于其它的个性化。它承载的是一个艺术家从审美感受开始,到思想观念的形成,及精神气质等一系列内在特征的外化。所以,西方绘画很讲究风格,而中国画不大讲究风格,而注重品格,注重人格化的东西。毫无疑问,在有关中国画风格论这里,所谓中国画的风格,就是一种人格化风格的形成过程,它是画家超越初期的幼稚,摆脱模式化的束缚历程,趋向于最后成熟阶段的标志。 雅俗共赏,是齐门绘画的大概风格,这是世俗和高雅两个群体认识上的折中。他们的认同点,定在取舍雅与俗的中间。这是一种一看便懂的欣赏体验,和百看不厌的审美状态。这两者的转换看似有其必然性,但是,它的难度不仅难在专业与非专业之间关于审美的趋同,而难度尤难在简单易懂久而又不生厌。所谓的“雅俗共赏”四个字,前者的雅,是自唐以来文人画所秉持的审美理念。后者的俗,则是相对前者所不足以观的统称。若让两者兼容,是需要相互颠覆各自的审美观习性,这无疑是水火不容的一件事。…… 二千多年前孔子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见《论语·阳货》。后人说这是孔子贬斥有关“俗”的思想,实际上这是孔子一贯崇尚“和谐”的审美立场。他所谓的“郑声淫”,这个“淫”字,即指其太过渗进了俗的成分。他是在担心这种俗声、俗调一时成为风气,唯恐把“随俗雅化”变为“雅随俗化”而已。 这种观点到了宋玉的时代,几乎以媚俗为羞,脱俗为高。他向楚王说起“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比喻后又说:“……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于是“曲高和寡”,便成了一些人假借高雅之名,眩人欺世的诡辩之辞。而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的不同,并不是风格上的差异。我们或从《诗经》中,关于风、雅、颂、三者找出答案。其时的“风”,不过是“下里巴人”而已。……由此可知,决定其艺术品位高下的,不仅仅是表面风格,它是与风格相表里外的内涵所决定的。…… 胡翘然是绝对大器晚成的画家,他的晚成,几乎带有改革速度与速成的特征。……客观地讲,从他七十岁之前的书画风格中,没有看出能成为一代大家的任何迹象。……严格意义上讲,这一切都在他七十五岁之后才露出了端倪。……对于这一现象,颇象一代学人,六十岁以后以书法突起的沈曾植。而近代画史上,还没那位大家能与胡翘然这一现象与之对应。艺术上以“勇猛精进”这四个字,形容晚年的胡翘然是最贴切的。而就以往艺术规律看,这一切几乎完全不能是人为的冒进。…… 人们研究中国艺术风格的发展历史,或对于艺术史上有关风格产生与形成的研究,往往是以朝代的更换来论风格的变化。而艺术家个人风格的形成,对于每个艺术家而言,除了历史形态的某些变动以外,文化本身的演变、和艺术规律自身的发展,对艺术家的影响更为重要。…… 从胡翘然年进入北平国立艺专开始,在后来二十多年中产生的上万件作品,几乎是全部被他焚毁掉了。这种原因也许只有一个:可以说是因为其艺术上没有风格的确立。从“自毁其画”这个事件中,也说明了就绘画行为上,他对于没有自己风格的劳动,在生产价值上所持有的一种态度!……这一点在他后来的艺术创作上,是最为可贵的一种人文品质,与崇尚的艺术创作精神!…… 确切地说,从目前看到他于年创作的《山村新貌》《养猪积肥》以及年以海阳县十二中学写生素材创作的《同学饲鸭图》,和后来获烟台地区“中国画写生展”一等奖的;年创作的作品《兰家庄养鸡厂》。这些都是以当时农村风物为创作的对象,其中还有多幅《迎曦图》、《农村风趣图》及他在年旅途中写生创作的《蓬莱渔汛》和《院中饲养的长毛兔》等等。……这些作品明显地展示了他从年到年,艺术渐变中的一些契机。从这二十年中所留下的作品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就艺术风格而言,是其倾心着力于“思变”与“求变”的过程。尤其是从他“退休”开始到这些年间,是他突破以往“传统”最为关键的一个时期。……而这三十年变化的关键,则是他从书斋进入了田园。也许正是这仅仅的一步之遥,使我们能从胡翘然艺术成功的交叉点上,感悟古人于中国画上导引后来者所谓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这一“不二”法门的所在的艺术创造真理定义!…… 从年到年,是胡翘然绘画风格的完全独立的十年。而这期间的后五年,几乎是风格日趋完善的一个阶段。也就是说从年前后,己经完全从齐白石、吴昌硕、王雪涛一路写意中脱身。(而在这之前的很多年,尤其是王雪涛的影子始终是存在的)。最为代表性的特征是,对一些题材的表现,他超越了他以前包括史画上的任何一个大家。如雏鸡、麻雀、燕子、白菜、等等。从到年去世前这十年,是他艺术从风格完善走向完美的十年。虽然在这期间,其风格略有几次小变,但凡所变,无不是向着尽善尽美,向看人生最后的灿烂而粲然一跃!…… 一千年的刘勰早曾说过,“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见《文心雕龙》。宋人郭若虚在其著作《图画见闻志》里说“人品既已高矣,气韵不得不高。气韵既已高矣,生动不得不至。”十八世纪中期,法国学者布封在《论风格》中,提出了“风格即人”的观点。清刘熙载《艺概·书概》则曰:“……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黑格尔认为个别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有可能完全是他人格的一些特征。…… 以上这些中外贤人学者的言论,是有关文学、绘画、书法风格与人格的关系。他告诉我们风格的形成,是由艺术品的独特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结果,是做为创作主体的艺术家个人的个性特征的自然流露。一个艺术家他的自我的内在品质、思想、精神如果很高,那么在他的作品当中,就自然而然地赋于思想性和高尚的精神品质。有了这种内涵,作品就会生动,才会变的富有美感。 他还告诉我们,风格不是想做就能做出来的,它体现出的是画者本人的个性与艺术才华,风格更不是随心所欲、无所顾忌,风格是盛开在文化底蕴之上的花朵。翻开古今中外绘画史书可以看到,世界上每一位具有独到艺术风格的大师,其灿烂辉煌的作品,无不是扎根于坚固的文化厚土之上的。…… 胡翘然绘画给人的综合风格,是他人格加上综合艺术修养的展现,是雅与俗的历史流变。按中国文化发展传统,每一次的开新必在复古中进行,蔑古开新则必流于时俗。古人把“雅”与“俗”对立看,“雅”是通于古今的价值观,“俗”则仅限于当世的一种方法论。而通才对此不仅不相互排斥,而是可以把两者统一起来。所以一味地尚俗者,则只知道眼前与当世,一味地尚雅者,则不知古今是一脉相承。前不见无古人,后无视来者,是只知道求变,不知道变中的道理。所以,历代那些附庸风雅的浅薄者,常常从雅陷于俗,而又不知道为什么。…… 要知道“随俗雅化”,是要化俗为雅。雅高于俗,这是艺术高低之分的基本认识。“随俗雅化”,是从大俗之后的脱俗之变。而这种脱俗的“雅化”,是高于原来的的个“雅”的。今天还有人指责齐白石的“俗”,实际上这种认识,正好印证这些人本身的肤浅,他们是看不懂这“俗”中之“大雅”的。…… 对于齐白石与胡翘然师徒而言,“随俗”是一种大境界,“雅化”一种大能力。“随俗雅化”才是他们艺术上的最大风格。“家样”是大风格之下的百变“观音”,他化身千万、又无所不在。…… 中国文化的精义,是儒学贯通古今以求“常”的理念。这个“常”,可以解为《老子》的“道”。它是一种在不变中的变。它又是一种在变中的不变。这或许就是世相的常态化。而正是这种历史中的“常态化”,它在文化的深层中,起到了作用于艺术规律的发展与演绎,而风格不过是这变化中的一种外在的显现。在中国画的探索与创造上,是其艺术内蕴外化的一个表相。…… “胡家样”就是在这种变与不变中产生的。而“胡家样”的表相,其背后亦有着顺应与符合艺术规律的运行,和以深厚的文化底蕴,来做为他培植艺术创新的土壤与根基!…… “胡家样”的章法 谈“胡家样”,首先是他的“章法”。这是他有别于同代画家、或越过同代画家进入画史的资本。而当今画界诸多法家,第一眼看到胡氏作品时,往往会大呼此公不得其法,云云!。所谓“不得其法”,就是说胡翘然作画全然不懂古人的章法。既然一个画家作画连章法都不入规矩,何需再论其它。也就是说,他的章法往往首先把人们挡在了门外。…… 关于章法,或何为章法,它是中国古代品评绘画作品标准法则。是南齐谢赫最早在其所著《画品》,关于“六法论”中提出来的所谓的“经营位置”。也就是后人被普遍称为的“构图”。而今天关于这几个字的理论之多,真可以用“入则充栋,出则汗牛”来形容。……“经营位置”这个词汇的出处,最早是来自建筑。经营,原意是营造,位置,是指测量的地位或安置的行动。如《诗·大雅·灵台》:“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而成。”。这是一首记述周文王建成灵台和游赏奏乐的诗。经是度量、筹划,营是谋画。谢赫借来比喻画家作画之初的布置构图。其中“位置经略,尤难比俦”,是安置的意思。唐代张彦远说“至于经营位置,则画之总要”,他把安排构图看作绘画的提纲统领。位置须经之营之,或者说构图须费思安排,实际把构图和运思、构思看作一体,这是深刻的见解。对此,历代画论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 古人论经营位置,主要是讲上下的位置、左右的位置、对角的位置。即所谓的占天式、占地式、中心式。如南宋时,有人把马远与夏圭两人的构图称为“马半边,夏一角”。似乎没有具体的指导步骤,而是多用“比”、“兴”的方法。比如,将构图的关系和社会人际关系做比较。在画面的物象安排处理上,要讲究社会伦理、尊卑高下、主宾有别的。是要符合儒家思想关于“礼”的关系。从唐《步辇图》、宋《韩熙载夜图》开始,虽然这主要指人物画的创作,但在山水画与花鸟画的章法运用上也同样如此。如《芥子园画谱》中所谓的群山环抱,如君臣朝祭之势,主峰是君,群峰是臣等等。…… 古人把作画的章法,又等同于文章的“八股”之法一样去理解,也讲究起、承、转、合的关系。把“起”、“承”、“转”、“合”具体到一幅画当中的每个环节。所谓“起”,是主体展开气势和方向,“承“是按主势和起势增加变化。“转”是指打破主势增加矛盾改变方向。“合”总结全局复归主势的呼应关系等等。…… 古人还将构图称为:“置陈布势”。因为“势”曾是古代书论冠以文章的一种称谓,如卫恒的《四体书势》,这里的“势”包含格局与气象的意思。唐太宗在《书论》中,“以阵喻书”,把章法与阵法等同视之。它里面有虚实,有彼此呼应的变化关系。在书画的构图里面也讲究这种方法,在画面中强调物象之间所形成的呼应之势,使的它们之间无孤立之感,这样才能达到气韵生动。 古人有“知白守黑”、“虚实相生”的说法。这是中国艺术的精神,它落实到中国画的章法里,就尤其重视“虚与实”的关系。“虚中有实,实中有虚”,它往往成了衡量中国画的关键。观者往往从实处着眼,虚处留意,这和诗文、音乐、戏剧、一样,它引导人们在虚实转换中对更大空间的冥想。以期进入一个意外之意,画外之画,象外之象的“虚境”之中。这种“虚境”,就是“空故纳万境”的境界。这种“观物味象”式的论述,在古人的画论中很多,它更多是启发人们对“物”与“象”的认知。 构成胡翘然绘画章法独特的因素,主要有五种;1:“别出心裁”从形式上突破一种规格。2:立意与变化的统一。3:计白当黑的空间处置。4:布势破势与造险破险。5:书法穿插的韵律感。实际在章法上,古人所有论述阐述到了今天,在胡翘然看来都不过是人云亦云。“不泥古法,不执己见”才是形成“胡家样”所有自家面目的根本,章法是他解决的首要问题。 1:“别出心裁”从形式上突破一种规格。 所谓从形式上突破一种规格,是指胡翘然绘画的幅面多以传统的“三裁”规格为主。而他对章法的突出成就,亦是对此规格在其表现上的突破。我们知道,中国画所供选择用的纸张和所要表现的形式很多。它同样是构成形式美的要素之一。这其中也有很多种变化,如中堂、条幅、条屏、斗方、横披、手卷、册页、扇面等多种艺术形式。……胡翘然画作数以万计,形式亦丰富多样,然而有绝大部分形式是“三裁”类。造成这种形式的单一,与他生活条件有很大关系。由其是晚年受“蜗居”空间的影响,若画大幅的作品是一件很困难的事。而“四尺三裁”这种大小的纸张,就成了他因地置宜最为得力的规格。其实“三裁”虽然属传统规格,但传统中的前人,并不看好或也不看重这个格式。因为从笔墨的书写性、与欣赏的习惯上,他们早就从实践中看出了这种规格的局限性,它实际上只是册页纸的放大。尤其是近代海派所风行的长条竖幅,更有利于笔墨表现空间的延伸,更适应S型构图力度与气韵的流动。因此,从吴昌硕到齐白石,都极擅长运用这种形式。尤其是从展览与陈列的效果看,这种长条式的形式更具备它的大气势效应。所以,后人在论述这类形式的作品时,往往以老笔纷披酣畅淋漓来形容,而这种气象绝不适宜在“三载”规格上的运用。这就使得以“三载”规格的作品创作无意中受到了因规格带来的限制。而晚年的胡翘然则突破“三裁”的诸多“不宜”,他似乎是在有意要在这单一的规格中,体现了风格形式的多样化。而最终使人注目的、或谓接受就是这种构图的样式,并无一丝局促与苟安的感受。其形式美感的视觉张力,反映了一个画家的修养、技艺、才略,它是一种精神理念的综合表现,并形成了由立意——为象——的整体格局,从而开创一个规格上的完整体系。对胡翘然,这不仅不是一种孤立的形式表现,而是决定了其创作的成功因素。 2:立意与变化的统一 胡翘然绘画的章法是极为丰富多变的。当然这种多变,源于他对大自然素材领悟,以及其观察事物那无限丰富性的一面。同时,他在绘画章法尤其是在花鸟画的构图法则上,更讲究从画境立意的需求入手,而非只着手于眼中物象的排列。这种表现方式是一种意化之后的“意在笔先”。亦可以说这是一个画家认识自然后思维表达的体现,也是现实生活转化为艺术生活的过程。 胡翘然深刻体会到,花鸟画的感人表现,决不是取决于形态上的“惟肖”与准确,而是立意后的心灵感应。这是一个不断深思与探索的历程,其构成的形式上的呼应,不但需要表现出认识自然之美,还应体现出作者独特的情思之美。在体现立意与传神的境遇中,强调内在情感的传达。而这一切都需要摒弃传统章法上的程式化图式,并突破传统绘画作品中感觉呆板的取景习惯,以寻求摆脱常规构成中的那些图解式的说教。 毫无疑问,胡翘然对章法的主观认识与思维的方法,是不以传统经验为主导的,这正是产生他的构图形式的要素之一。这种构图思路,是他从客观自然的变化中,在对立统一规律中寻求的一种新的表现风格。这种立意方式和构图方法的又一统一,成了广大欣赏者所愿意接受的艺术图式。所以说,立意与变化相统一的章法,对艺术创造过程中画境的表现尤为重要,而立意与章法的相互依托产生的形式美,才更能显现其感人的魅力,这种优势在胡然绘画的章法上显得尤为突出。 3:计白当黑的空间处置 画中的空白,与一张素纸的空白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画的空白绝不是空洞无物、可有可无的,而是中国画形式语言的重要构成要素。根据不同的描绘对象,这些空白的精心布陈,将给人以丰富联想。虽无笔墨的点染,却有画家精神的寄托、情思的流露。它既是空灵的、又是博大的。这一点在胡翘然的章法上更为明显,他在运用前人所谓“疏可跑马,密不通风”的方法上,往往更具有大疏大密的对比。包括聚与散、动与静、明与暗。 在胡翘然画面的构图中,常留有大量的空白。他秉承了尤其是宋元以来的文人画的章法特征,而舍去逸笔草草的荒率,又能够兼顾其形神。尽管,在他很少的一些画中,对空白的处理,也有意识去触及文人画“冷逸”的一面。所描绘的自然生命,常常呈现在一片虚白里的一花一鸟,与洁白的素底相互映衬,造就了中国画特有的空灵、简远、虚静的艺术境界。但是,这与八大构图异于常人一样,他不仅是构图本身与常人的差异,也不仅是章法本身与常人的不同,其差异还在于状物之疏散与孤立。纸上留下大面积的空白与空间,给后人视觉所产生的印象错觉。……今天很多人学八大这种“构图”法,并用套用一个词语叫“构成”,而除了笔墨的空洞在这种构成下尤为苍白之外布别无它物。……你只要有一定的见识,面对八大的真迹,你才知道八大之所以能倾倒后人的,除了他绘画的精神气质以外,就是他笔墨本身的精湛。所以八大仅凭笔墨的独立,亦足以傲视百代。我想那些学八大摹仿八大的人,应该在笔墨这一关上下下功夫,否则空费时光绝无成绩。 4:布势破势与造险破险 “胡家样”章法的整体特征是“奇”与“险”。他深知要想使章法获得变化,就必须巧妙的处理空白、疏密、虚实之间的关系。所谓空白是无画处,是虚处,是疏处。而琉与密、虚与实之间,皆是相对的空间感受,并非是具体的空间位置,正所谓“虚实相生”、“奇正相生”、“无画处皆成妙境”等等。这不过是要求做到疏密有致罢了。而要想打破前人关于构图的法规,就必须重新研究疏密、聚散,的关系。而如何能使画面得到空灵变化的意境。绝不仅仅是如老生常谈的“疏可走马、密不透风”那样简单的一个空洞式的概念。 前人在章法上讲究的“相成相破”,它含有矛盾统一的意义。“成”相当于统一,“破”相当于矛盾。统一而不变化是呆板,变化而不统一是杂乱。要统一中有变化,变化中服从于统一。整个构图以此为基本规律,多采取均衡取势,而避免对称。胡翘然实在是深谙其理的,在他笔下多是“画三不画四”,三是奇数,四是偶数。画偶数的物象易流于均匀整齐,奇数即可以打破这个局面。奇和偶也是相辅相行的。“惨淡经营”方可成。这是一种贯穿中国人宇宙观的思想,是“阴阳相生”、“虚实互动”。它是从矛盾变化中产生的虚与实。因此,唯有打破以往所有的定式,才有可能找到一种新的不是章法的章法。就在这样一种处意中“胡家样”慢慢脱壳而生。这个时间大约在胡翘然七十五岁左右,这是孔子形容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年龄。孔子这句话对于七十岁以后的胡翘然来说,就是心中要有想法,并随着心中的想法走,怎么想怎么干,怎么干怎么对。因为,凡事虽然有矩,但这些“矩”并不能妨碍思想和形为的自由,而这种不“逾”是顺心而为,这恰恰就是顺乎自然。这是齐白石与胡翘然,“衰年变法”的成功之道。 5:书法穿插的韵律感 在中国传统文人画当中特别重视诗与书印的有机性。题款、钤印,可以起稳定和谐构图的作用。所以,中国画与题款、钤印、书法、诗词的相互补充、能相互增益是缺一不可的。画中的物象,往往占据画面边角位置、或对角空间,其间以题款承接。而书法的题跋在胡翘然的画中完全具有与画几乎对等的作用。把书与画称之谓计白当黑,将字里行间的虚白处,当作实画一样布置安排,黑白两者遥相呼应。调节空白使之不觉空虚,实处又不觉闭塞。如书家邓石如论书曰:“字划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他以书法艺术的故有章法制造空白,甚至分割空白,这是胡翘然章法神乎其技的高妙处。 中国画空白的地方,不是空闲多余的地方,它是作者故意造出来空,或是作者有意隐去的实。并非不重要,而是代替了那些需要减舍的物相。潘天寿曾不无感慨地说:“黑无白不显,白无黑不彰,故水墨之画,更不能离白色之底也。”。如胡翘然画梅、画荷,他利用梅花与荷花的枝干的特性,画面上常常是一枝花随意生出,以大片书法穿插交互,远观给人以飞花撒雪,落英缤纷之感。还有的整幅画面,除去一枝花,落款之外皆为空白,“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给人以丰富的艺术联想。 胡翘然的书法,在题画落款的表现上,是超出他独立的书法创作的。此外别无一物,大片虚白,干净之极。这些空白,给人亦天亦水亦雾亦幻的朦胧感,也给人以闲适宁静若有若无的迷茫感,似乎时间已然凝固。这样的画面无一丝粘连,所描绘的一切皆能独自呈现出其中的意趣,似乎这切都怡然自得而不受世事的纷扰。比如他笔下大量的荷花作品,除了花与叶之外,所留空白往往一片空明。墨与色的边际透着淡淡的光线、轻微的和风,沉寂之中可听到蜻蜓翅膀与小鱼戏水的声音。当然了,聆听这声音,需要闲适的心态、纯净的灵魂,正如庄子所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虚者,心斋也。”听之以耳,莫如听之以心,听之以心,莫若听之以气”。……的确,这是一种天籁之音,宁静之中的声音,侵入人的灵魂深处。 胡翘然笔下世界是一个极其疏朗的艺术空间。在视觉上,他笔下的章法空间永远是那么疏朗,那么空灵剔透。胡翘然章法他最大的成功,在于能以熟练掌握以书法去调节彼此的的关联,使之产生一种运动感、节奏感和韵律感,在布局中使画面更加富有变化。这一点板桥老人之后,胡翘然做的最好,并且是最成熟的一个人。在画史上仅就章法论,几百年来真正能与前人与同代拉开距离的,并能造就其独立风格的形成与成熟,唯胡翘然一人而矣。 这样的理论解说很是抽象,但凡是对胡翘然了解自可意会其中的奥妙。而尤其为难的是,胡翘然在章法上有些玄妙之处,非是语言能说清楚的。……所以,中国画的写意性,和中医的一些道理一样,正所谓“医者意也”。这种对“意”诠释是很困难的,它可能不适宜于一种逻辑上的推理,但这又不妨碍我去用理论去接近它。因它的理论本体亦是写意,其本质在“似与不似之间”,所以还要以“似是而非”去解读它。 “胡家样”的题材 作为20世纪中国画史上坐标式的人物,齐白石的全能是罕见的。他以旷世的才学,在诗、书、画、印、中游仞自如、且风貌独具,给后学带来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就驾驭花鸟画的题材而言,后人能在这样一种绝境之中,另外垦荒一片属于自己的“自留地”谈何容易。环顾左右,不得不承认,在半个多世纪的空间之中,胡翘然是继白石老人之后的又一座巅峰。仅就他花鸟画题材的丰富性而然,毫无疑问,他是继白石老人之后的又一位集大成者。“胡家样”中的花鸟画不是“标本”科目的图解,而是一片自然生机的物象。与同代的花鸟画整体风貌相比较,从写意花鸟画的笔墨章法与意境上,都有其独特的一面。而“胡家样”的形成,从题材到样式的变化上,较同代画家则尤为突出。毫不讳言,胡翘然掌控了齐白之后的中国写意花鸟画的总“态势”。 大自然中花鸟的形态可谓千奇百怪,它们之间的种种图景是无穷尽的。这些处在变化当中的各个侧面,被历代画家“传移摹写”了千百年。如何寻求一种新的艺术表现,以对旧题材花样的翻新,这无论抽象还是具象,由于时代、环境、空间、文化、的不同,它都是画家永远面对的课题,胡翘然的着眼点即在于此。 绘画的风格,具有多样化与同一性的特征。大自然无限的丰富性与多样化,为艺术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胡翘然的绘画题材广泛,名目繁多,仅在花鸟画的范畴之内,几乎是“包罗万象”的。他不仅能表现客观事物的多样性,而且能够系统性地予取予求。这一点与古今文人画家,在价值取向上是有所不同的,他更偏重对自身的直接体悟与描绘。他与其师齐白石一样,一生不画没见过的东西,所画的基本是以他的视野所及或亲手种植过的。从胡翘然国画题材汇总量来看,初步统计有六大类别,大概近三百个品种。 1、花卉植物类:梅花、牡丹花、月季花、芍药花、兰花、荷花、莲花、菊花、茶花、红玉兰、白玉兰、喇叭花、玉簪花、凌霄花、紫藤花、樱花、木棉花、桃花、杏花、梨花、海棠花、蜀葵(步步高)、万年青、水仙、仙客来、雁来红、迎春花、鸡冠花、苦菜花、狗尾巴花、君子兰、美人蕉、郁金香、紫薇、木槿、百合、萱草花、鸢尾、茉莉花、七色堇、勿忘我、玫瑰、曼陀罗、风信子、桂花、绣球、玻璃海棠、蝴蝶兰、台湾竹、蒲公英、野花、竹子、柳树、松树、槐树、枫树、柏树、红叶、杨树、芭蕉、铁树、棕榈、柞树、桑叶、灵芝、…… 2、羽毛禽兽类:鸡(公鸡、母鸡、童子鸡、雏鸡)、珍珠鸡、斗鸡、鸭(大鸭、乳鸭、水鸭、旱鸭)鹅、鹌鹑、鸽子、鸳鸯、雉鸡、竹鸡、麻雀、竹雀、云雀、燕子、竹燕、乌鸦、八哥、鹦鹉、大鹏鸟、鹰、雏鹰、猫头鹰、鱼鹰、大雁、芦雁、天鹅、鸬鹚、翠鸟、野鸭、喜鹊、黄鹂、仙鹤、绶带鸟、白头翁、海鸥、雎鸠、鹭鸶、无名野鸟、兔子、猪、猫、狗、牛、马、羊、狐狸、老虎、猴子、老鼠、松鼠、大熊猫…… 3、水族类:鳖、乌龟、刀鱼、鲅鱼、青鱼、鲢鱼、草鱼、鲤鱼、鳜鱼、红加吉鱼、红鞋鱼、青蛙、金鱼、灰鲶鱼、黄鲶鱼、鲫鱼、罗非鱼、泥鳅、白漂鱼。花蛤、蟹子(活蟹、熟蟹)、淡水草虾(活虾、熟虾)、海水对虾(生虾、熟虾)、芦苇、水公子、水草、水菠菜、菖蒲、香蒲、水葱、慈姑、红蓼、梭鱼草、水苔、浮萍、……4、瓜蔬粮果类:黄瓜、丝瓜、南瓜、大枣、黄金瓜、栗子、苦瓜、甜瓜、冬瓜、饺瓜、西瓜、梨、苹果、海棠、樱桃、葡萄、葫芦、桃子、石榴、柿子、莲蓬、枇杷、枸杞子、山楂、荔枝。稻子、谷子、高粱、黍子、大豆、玉米、玉米穗、麦子。月饼、粽子、鸡蛋、韭菜、芹菜、大白菜、小白菜、青菜、竹笋、藕、青葱、辣椒、蘑菇、菜豆、眉豆、水萝卜、茄子、胡萝卜、豆角、芋头…… 5、草虫类:螳螂、蝌蚪、蜻蜓、瓢虫、天牛、甲壳虫、蜘蛛、蚂蚱、蝈蝈、蛐蛐、蝴蝶、蜜蜂、马蜂、蚯蚓、蚂蚁、蚊子、青虫、知了、葫芦蛾、蜗牛、水黾、蚕、土元、豆娘…… 6、杂属类(应景):人物、山峰、悬崖、炉子、水壶、酒壶、杯子、蒲扇、草垛、麦捆、火苗、蜘蛛网、石头、云彩、水库、江、大海、池塘、帆船、舟、花盆、花瓶、蝈蝈笼、粮囤子、鸡笼、瀑布、茅屋、瓦屋、太阳、月亮、龙、盘山路、长途公交车、拖拉机、自行车、看瓜棚、篱笆、雨伞、书包、毛线团、布玩具、毛笔、电线、鞭炮、院墙、门楼、盘子、盆、碗、筷子、草垫子、竹筐、晾的衣服、脸盆、铁锨、镢头、簸箕……(此为胡翘然题材的初步统计,其数量与齐白石仿佛,远远超过白石门下的其他所有弟子,在中国绘画史上亦极罕见。这些题材只是以目前所见到两千余幅画为依据,尚有近万幅作品散落在藏家手中。所以,关于胡翘然的题材,今后一定还会有所新的发现,其数量亦处在继续补充中……)这些都是“花鸟画”范畴之内的素材,从以上罗列的这些动植物中,我们亦可以看出,一方面是胡翘然的绘画表现欲非常强,对素材的范围有一种全面的掌控愿望,对题材的驾驭有一种天生的自信力。另一方面,除了他没见到的东西一外,他并无有意识地故意避开名家标志性的题材,只是略有侧重而已。有的即使在笔下出现,其表现方式也绝不是摹仿,如他笔下的虾、蟹、猴、牛等等。他不是在避让古今、而是去选择独辟蹊径。在花鸟画领域,有人对齐白石与同时代的花鸟画家涉及题材做过统计。齐白石涉及的题材大概在二三百个左右,而后人最多的也仅仅只是这个数量的一半。……要知道“胡家样”里的这近三百多种题材,只是胡翘然在花鸟画范畴之内的“项目”。除了花鸟画题材之外,他山水画和人物画的题材也是有一定数量的。 在他的山水画中,有四时变化的不同景色,有古今向往的兴胜之地,更多的则是隅居一方的海隅迁陌,和开门见山的本土田园。他的人物画不多,但题材却能兼容古今。其中有高士、有顽童、有淑女、有酒仙,有痴男旷女,也有才子佳人,还有儒、释、道、亦有神、鬼、仙等等,其造型朴拙生动,既准确又概括,极为传神又不同于他人,完全是“胡家样”中独有的面目。 胡翘然这二百余种动植物绝大部只是题材,而同一题材所产的作品有的可能会衍生出上百种之多。虽然每增添一种动物或昆虫,画面会多一分情趣,但它同时也在增加一份难度。这难度不仅表现在动物习性与植物品性的配合上,更难的是对于笔墨造型、比例、动势、形态与色彩的配合等等。这不是仅仅凭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花、鸟、昆虫的喜欢,就可以很好地从艺术性、从技术难度就能轻松解决这些问题的。诚如《宣和画谱》中曰:“诗人之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律历四时,亦记其荣枯语默之候。所以绘事之妙,多寓兴于此,与诗人相表里焉。故花之于牡丹芍药,禽之于鸾凤孔翠,必使之富贵;而松竹梅菊,鸥鹭雁骛,必见之幽闲。至于鹤之轩昂,鹰隼之搏击,杨柳梧桐之扶疏风流,乔松与柏之岁寒磊落,展张于图绘,有以与起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若登临览物之有德也。”…… 所以,古人把艺术创作不仅是看作一份精神的劳动。同时依据的还有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人与心灵的关系。任何艺术形式都是随着审美需要而产生的,一种好的花鸟画题材的产生,除了它自然美感的特性之外,还包含画家丰富的生活观察,娴熟的笔墨表达能力、深厚的文化修养,以及互为锤炼而成的一种综合能力。所以说,这种创作本身就是一个综合塑造的过程。画家在创作中,须从以往的理论、流派、风格、形式、技巧上下工夫,在比较与概括升化“自我”,以“别出心裁”之心去固定“标新立异”之本。以此体现“自我”在艺术创造性上的多样化的时代模式。 “胡家样”的产生绝不是孤立的,他是中国画走向的又一个高度,这个高度是胡翘然从齐白石上溯古代艺术高度的结果。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人们对花鸟画的认识和情感,是不能停留或徘徊在古人那里。不应该去再重复青藤、八大、板桥、老缶、白石。这是由于时代不同、认识不同、情思与理趣不同所决定的。那种精神上一味仿作古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作品,不仅不能引发当代欣赏者的情感共鸣,而且这种“东施效应”,会使一个时代的艺术因无创造力而失去灵魂。人们对东施的耻笑不是她自身的丑态,而是这种审美意义上的盲从与无知。 可见生活情思所引发的情感共鸣,不仅反映了画家的创作态度和方法,同时也反映了时代的变化与需求,以及新的审美价值的相关取向。为此,胡翘然他能够化景物为情思,以新的视角、观念、主张及表现手法介入其艺术的创作,使其笔下的花鸟画作品,产生了新的艺术魅力并达到了感染人的艺术效果。一个艺术家,在一两个或十几个题材上做到游刃有余,已属不易。而胡翘然竟然在几百个题材中都能够做到比肩前贤,睥睨时彦,如此造化实在是令人惊叹不已!…… 欣赏他的这些千姿百态的作品,时有令我们意想不到的惊讶与欣喜,例如他笔下“荷花的世界”、“燕子与麻雀的世界”、“大鸡与雏鸡的世界”、“猫与狗的世界”、“梅兰竹菊的世界”、“在水一族的世界”、“五谷丰登的世界”等等。有的细数只几个题材,而经过胡翘然之手产生出的“胡家样”几乎是无穷的。更有蜻蜒、蝈蝈、蚱蜢、螳螂、蟋蟀、蝉、蝴蝶等等草虫点缀其间,使画中的情趣更为活泼幽深。若就所描绘的草虫之多来看,他不及齐白石。白石老人笔下的草虫即使全部以“工”而成也透出十足的“写”。而当下画家能画出草虫的质感就已属高手,其中的趣味已没人能写出。而胡翘然却远远不止如此,他凭写意的手段能将草虫的性情传达给我们。若讲写意描绘草虫的传神之妙,我们认为后者可直追乃师。胡翘然对客观事物与主观情感方面,有着超常的、极为敏锐的艺术观察力。其表现力、感悟力是惊人。对于燕子麻雀这种与人若即若离小鸟,要想做到细致入微的结构刻画并不难,难在飞与栖的神形兼备。燕子麻雀是“胡家样”独有看家本领之一,这点在画史上是空前的独家面目。 略通画史的人都知道,对于千载画史当中任何题材与样式的突破,实在是一件难之又难的事情。而在“胡家样”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题材与样式,是可以与画史当中的任何一家去进行比较的。比较的目的不是比孰高孰低,它的意义在于从中国画的历史找出其中的必然,这就是创造与发展的规律。时代在变,今天采取什么样的艺术表现手法并不重要,关键是最终所达到的艺术质量与效果如何。在“胡家样”的艺术世界里,我们会看到了一种生机盎然的生命景色,看到了祥和融洽的生活乐趣,看到了自然万物对于我们人类的重要性。在胡翘然的所有题材里,诠释的是对于大自然万物的一颗爱心和众生平等的生命关照。 从风格到章法,从章法到题材,从题材到样式,这是衍化生成“胡家样”的一条完整生物链。对于“胡家样”样式的整体解读,它将是一项浩大的学术工程,今天我们无法完成其细致的图说,只能梳理一个大概的框架。在这大概的框架之内,我们发现,花鸟画题材与样式的表现,终就不是只对视觉题材的变化与更新。关键在于在状物的过程当中,通过画家的技艺、学养、天赋与哲思而综合地表现出来。否则,由现实生活直接转化到视觉创作中的形态表现,就不会产生出物趣的感觉,这就是照相机诞生以来并不能代替以视觉绘画的原因。画家完全可以在“状物抒情”中做到“借题发挥”,而相机不能从视觉之外来充实画境。这也是中国画艺术在创作中传达情感过程的基本手段。当代画家可以借助任何外来工具附助视觉,但中国画艺术语言的表现,所运用的都是笔墨审美表现的个性介入。这就是说,创作过程中,笔情墨趣触碰产生的再创作,是任何工具都无法代替的,这种得意忘形的状物表现是心灵的物化。在这一种笔墨迹变的发展中,使中国画表现风格从章法到形式,最终突破了外形轮廓的拘束。在似与不似之间,使情感、审美习惯与视觉感受都获得放松、自由与解脱。并通过笔墨的偶发性与自律性,在笔墨趣味中获得一种情感的释放。并在精神上领略其无穷的奥妙,使板滞浅显的形象图式活泼起来。于灵变而传神之中,让内涵的显露趋向更富有哲理。因此才有可能使绘画由一种题材的模式化,走向了以抒情为创造的手段与方法,由此产生出了千变万化的不同样式。这就是胡翘然从风格、章法、到题材及样式变化上所超出常人的奥妙所在。 与其说他是在创作,不如说是上苍与天才的一种契合。 近三百种题材,上万个不同的样式,构成了胡翘然在中国画艺术上蔚为大观的创作体系。…… 在古代、近现代、当代的画家阵营里,齐白石之外能堪与匹敌的,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 如是我谓;白石之前无此人、白石之后唯此人!。 .9.16于依然斋 文章版权归威海胡翘然艺术学会 所有转载请注明来源 长按下图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sz/5060.html
- 上一篇文章: 见多识广的你可曾见过蛋壳园艺,花草世界竟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