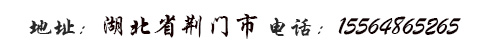神池桑梓情怀第16篇回望苍凉作者宗
|
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 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神池 这里有神池的经济、人文、历史、风土人情,立足故土,着眼家乡,动真情,写真人,记真事,讲神池故事,抒桑梓情怀 年05月21日 第十五期 回望苍凉 宗光华 作者刚参军的时候 父亲丢下我已22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一天也没离开过,我时而在脑际,时而在梦中,有时在饭桌上,有时在酒席前。逢年过节更是倍感怀念。我爱父亲,那是铭记在心中的爱,心中的痛。 父亲生于年。那是个战乱不断、民不聊生的年代,更是一个穷人抬不起头的年代。他是祖父唯一的儿子,他有两个姐姐,和他一样,都是苦水里泡大的,穷困潦倒伴随了父亲大半生。 父亲爱喝点酒,但一个穷字限制了他的酒量,从没见他豪饮而醉过。父亲的酒壶里多半是空的,偶尔有点也是为朋友和下乡的干部们预备的。我闻到酒味特别香,有时真想尝尝,但一遇到他那严厉如火的目光,就赶紧埋下头去。 “小娃娃,好好念书才是你的正事。”这是父亲声色俱厉的训斥。在他的约束下,我的酒量至今也不大。我十八岁前只和他喝过一回酒。那是我刚换上军装,从军的前一天。在县城招待所,父亲手忙脚乱帮我收拾好行李,已是万家灯火的薄暮时分了。他展了展腰,说:“走,喝点酒去。”顿时,我有点受宠若惊。长这么大,我第一次获得和父亲平起平坐喝酒的资格。 菜是简单的,只有一个像样的过油肉,其它的都是家常凉菜和老芥菜。父亲给我满上,父子俩一杯复一杯,谁也不说话。第一次喝酒竟有一种莫名的难受。“走吧,走的远点好,部队是个大学校,锻炼人,出了门就是条汉子了,自己要把自己管好。” 作者父亲 作者母亲 父亲仰起脖子又喝了一杯,他盯着窗外的夜色喃喃地说到。父亲这个铁骨铮铮的男人,平日里走路把地震得“咚咚”响,一开口说话那响雷般的声音能惊起一群鸽子,威严无比的目光让我望而生畏。而此刻,他的眼神里,竟漫漶着浓浓的忧伤与悲凉。我这次远行不是去上学,也不是当工人,更不是当官。而是当兵,当兵意味着什么,军人的前方是什么。这些父亲是一清二楚的。他虽没当兵的经历,但也是经过战争洗礼的人。他目睹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给八路军抬担架,救伤员,送弹药,押俘虏。他是年加入共产党的农村党员。那时党组织是秘密的,党员的身份也是保密的,他是把脑袋拴在裤带上挺过来的人。几杯酒下肚,我发现他的眼睛潮湿。在一个严厉沉稳的父亲面前,我有许多的话说不出来,连句安慰的话也没有。父亲默默地把酒酌满,递到我面前,“来,喝了这杯酒垫垫底气,从今往后,我管不了你啦,命运操在你自己手里,要尊敬首长、团结同志。不要忘了给家里写信,你妈最疼你……” 第二天,县武装部门口人潮如涌,送别新兵的亲人们依依难舍,千叮万嘱。我们这些娃娃们要背井离乡,远走天涯的时刻,作为父母们谁不牵肠挂肚的?我身旁的新兵们一个个哭的象刚断奶的孩子那样,泣不成声。我却尽量逃避父亲的眼睛,故意拿出一副“男儿提剑出燕京”的豪气,我不愿凄凉的泪水冲淡这悲壮的行色。 汽车发动,应该说再见了。我站在毫无遮蔽的敞车上,忽然看见父亲那双张望的眼睛,睁睁地站在那喧嚣涌动的送行队伍里,象个孱弱无助的老人般无语地望着我。那就是父亲,超出常人半头的壮汉。他身材高大,腰板笔挺,脸盘宽阔,双唇紧闭,象座铁塔似的。四周锣鼓喧天,鞭炮齐鸣,无论什么也掩饰不住他一脸的失落与惶恐。汽车开动,他情不自禁地向我挥了挥他那双大手。挥手之间,我的心如针扎。那一刻的我,真像断了线的风筝,从父亲的手中飞走了。我不由自主地举起军帽,微笑着向他挥了挥。父亲是刚强的,他硬是把眼泪咽在肚子里。 我是农民的儿子,这种源于血液深处的身份认证构筑了我生命最初的蓝本。要想有个城市户口,能安排个工作,那其中的艰辛是不难想象的,那是脱皮掉肉的事,是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才能完成的伟业。我得承认,作为一个农民,父亲是出类拔萃的。在我的眼里,他是个了不起的乡土哲学家,是个对人生有着清醒认识,对命运有着深刻洞察力的精明人。在十里八村,他以有见识、有魄力著称。他从互助组、合作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直担任村干部、生产队长。是当今中国算不上级别的最小最小的官。但这些毫没影响他工作的热情和积极性。为给乡亲们争得一斗米、一升面,公社主任要是拍桌子,他就摔板凳,书记要说撤他的职,他就说,老子不怕你。他从不在意那官不官的事。每当他昂首微笑着走进乡间时,人们都尊敬地和他打招呼,有的还留他吃饭喝酒。都说他是个大好人、正气人、有担当的人。 作者年轻时的戎装照 身为农民的父亲,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活一回,能够走多远,应该走多远。年,从农村党员中选拔南下干部,父亲已是注册了的人选,但因他没文化又被刷掉了。父亲对自己的命运丈量得很准,他象田径场上的运动员,自己该跳多高、跑多快都有足够的底气和把握。他的目标不是给儿子们盖几间房,给女儿们准备几套嫁妆,而是能培养出一个吃国家皇粮的人。他常说老子缴了一辈子皇粮,家里也得出个吃皇粮的,如今儿子吃皇粮了,这才是天公地道。父亲对村里的市属户既尊重又照顾,多有羡慕同情的成份。分粮给好的,安排营生给轻的。他说男人们在外,留下老婆娃娃挺可怜的,给点让点是应该的。父亲从不嫌穷爱富,他古道热肠,遇到上门讨吃要饭的人,他毫不吝啬,要啥给啥,只多不少,直到要饭的心满意足,声声道谢。 父亲被艰苦的农村生活,被黑暗的旧社会蹂躏够了的灵魂,蕴藏着火山一般的热情,他从艰苦的年代一路走来。过够了那种忍辱负重、吞糠咽菜、穷年累月的日子。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才大碗大碗地吃上了白面和大米饭。他笑着说苦日子总算熬出来了,跟着共产党艰苦奋斗40年没白干,值! 只有理解了父亲的经历,才能够理解他望子成龙的心情是多么迫切。他经历了贫穷,也经历了不少政治运动的清洗冲击。“三反”、“五反”、“四清”、“文化大革命”。但父亲身正清白,从没被清算,也没被打倒。他虽没读书,但他扛着一口气,天性不服输。凭他的记忆,当过保管员、大食堂事务长、生产队长。并学会了珠算、还会记账。每见他记账时,嘴里含着笔,苦思冥想,一笔一划,十分认真也很费劲。他能把家里家外的事情操持得蓬蓬勃勃,井然有序,但他始终怅然若失,常常独自感叹:“家里出不了个知书达理的人,这家人就没甚指望了,一笼鸡有一个会打鸣的就足够了”。 作为父亲的长子,他把打“翻身仗”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希望祖宗八代农民的老宗家能出个吃皇粮的,不再和他一样“吭哧吭哧”地和土坷垃打交道。父亲坚定不移地把一生的老本都押在了我的身上。可事与愿违,我让他一次次失望甚至绝望。从小学到完小,我的学习成绩还算可以,“三好学生”、“少先队队长”。上了完小的第一年,老师很看好,还让我当了班长。我的学习兴趣极高,父亲非常高兴。不料在第二个学期出了点事,那是个星期六的下午,我实在想家了(主要是饿的,想回家拿点干粮),到班主任那里请假遭到了训斥:“谁也不许回家,就你特殊啊,不行。”我悻悻地回到了教室,心里盘算饿着肚子,心慌意乱也念不成书啊,干脆,偷跑。一个大胆的决定马上就付诸实施了。星期一该到校了,一路上我的心里直打鼓,咚咚的,头上像顶了一篮子生鸡蛋,刚迈进教室的门槛,只见老师杏目圆睁,柳眉倒竖,两颊绯红。“同学们:宗光华同学从现在起就不再是大家的班长了!”一个女高音尖利的声音穿透了教室。我被撤职了。“撤职就撤职,班长有什么了不起”。心里是这样想的,可面子丢不起,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四周都是鄙视的目光射向了我,“伤心自比笼中鹤,剪尽翅翎愁到身”。 从那以后,我和班主任较上了劲,她教的是数学,我偏不学数学,只要看见她的影子就是恨!恨!!恨!!!,成绩一天不如一天,她气得骂我,我更是怒火中烧。我热衷于语文,对语文老师别样的敬重,我的作文经常受到表扬,有时老师拿着我的作文神采飞扬地读给同学们听。要考初中了,同学们都向往县中学(当时也叫羊鼻梁中学),那可是高师如云,声名赫赫,是多少娃娃们想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神圣殿堂,而我和老师的故意赌气,把自己害苦了,长大了才知道,自己害自己真的没深浅,考试结果名落孙山,羊鼻梁中学与我无缘,象牙塔擦肩而过。父亲知道后,比我更气更着急。但见他两脸铁青,像刚出山的老虎,眼睛瞪得怕人,闷哼了一声“废物”,如炸雷。“废物”,使我五脏俱焚,羞愧难当,浑身的不自在。父亲再没理我,我也不敢和他对视。 挥毫泼墨 就这样干耗着,多少天过去了,谁也不和谁说话。母亲耐不住了,“娃娃没考上,就跟你干活去,还值得你不和娃说话?你是想把儿子逼死吗?”“狗日的,老子种地大半辈子了,你还嫌咋地?”“咋了,世界上还是种地的多,种地又不丢人,没人种地,念书人吃甚,当官的吃甚?”母亲反驳说。老俩口你一言他一语地嚷开了,我见大势不好,拔腿就跑,三十六计走为上。我跑了,你们爱说谁说谁去。 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以后的苦日子接踵而来。父亲像押犯人那样把我押到绿油油的田里,金灿灿的地里,跟他锄田、收庄稼。不满十四岁的我只能锄两垄田,割两垄禾,腰酸背痛胳膊麻,汗珠珠一滴一滴地往下落,有时糊住了眼,分不清是汗还是泪,流到嘴里,咸。我终于醒悟,不该和老师赌气,赌气的结果是汗滴禾下土,粒粒皆辛苦。我心里由悔及恨、由恨生怨,由怨而产生对父亲的不理解,你自己没本事却想让我代你光宗耀祖,改换门庭,休想。这辈子我是跟定你了,受死就受死,早死早转世。 地里的活干完了,剩下的就是家里的事了。围磨。手推磨棍,转了一圈又一圈,转上一天也出不了那个圈。直转得头昏脑胀,两眼冒鬼火。这样日复一日地转啊转,要把一家人一冬一春的粮食都磨完了,面瓮填满了才算了事。那个累啊,别提了。现在的人们太幸福了,吃什么都是现成的。解放生产力,科学发展就是好哇。 父亲用心良苦,他是变着法子逼我回到学校去。可学校在哪里,父亲彷徨,母亲惆怅。一个农民父亲有什么法,只能两眼望青天。有一天,我发现父亲蹲在茅厕里,他头发一下子变的发苍,哭声哽咽,全身颤动,如同一头受伤的老狼。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看见他流泪,我心如刀绞…… 父亲不忍我干那样的重活了,他改变了主意。又是一个温暖和煦的暮春。他把生产队里所有的牛都集中起来,把精心制作的一根皮鞭交给了我。“娃子,放牲口去。”我高兴极了,那可是生产队里的美差,优哉游哉,自由自在。这也许就是父亲当队长的特权吧。 每天早晨,我把牛从臭烘烘的牛圈里赶出,它们摇头晃脑的,像是没睡醒,有的还张嘴呵气。它们那硕大的眼睛水灵而祥和,质朴而聪慧,狡黠而多疑。有时我的双目和某一头牛的眼睛相对的时候,它就会把两眼汪洋一般的善良死死地逼进我的眼里,是从未见到过的纯真和亲切。 在山峁上,在田野里,在山洼处,习习凉风送来,我坐在绿色的地毯上,翻开小人书时,牛的头已伸进鲜美的绿草丛中。有时它们会突然停下来,喘着鼻息呼呼地把热烘烘的气体喷到我的脸上;有时我被小人书中激动的情节所吸引,突然喊叫出声时,它们有的也会突然停下来,若有所思地端详着我的举动。有时,它们其中的一头还会笑,那笑的姿态十分好看,头扬的老高老高,咧开大嘴,露出白森森的牙,鼻子朝天一抽,“哞”地笑了,原来它的身旁有一头母牛,它是笑给它看的,可怜的牲口,也有传达爱情的信号。 夕阳西下时,它们肚子鼓鼓已经吃饱,就在我的身边撒欢,有的站着不动,像是有什么心事。注视着远方,有的相互挨着,好亲热的样子,有的竟然卧在我的身边倒嚼,心满意足,有的“哞、哞”!地朝我叫着,像是感谢我对它们的厚爱。这样的时光从初夏一直延伸到中秋。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牛是快乐的,它们的主要任务是吃,吃得膘肥体壮,生龙活虎,积蓄力量准备秋耕。牛高兴,我更高兴,约三两童伴,愉愉快快上山,高高兴兴钻沟,其乐融融。掏鸟蛋,捕黄鼠、捉圪狸,漫山遍野有我们的足迹,荡漾着我们的笑声。饿了烧山药,渴了山泉水,累了随地一躺,望着蓝蓝天宇,看着蝶舞蜂飞,听着鸟唱虫鸣,如梦如幻,此乐何极,幸福的象花儿一样。 站在那高山之巅,山风哗啦啦地吹,衣服鼓荡,像要被脱去似的,浑身舒坦,精神大振,“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感慨直涌心扉。有种天是老大,我就是老二的自豪和骄傲。我手执牛鞭,指点我的黄牛、黑牛、花牛;指点眼前的山川溪谷;也指点老天和老天底下的云朵。云的多种多样捉摸不定,有时白的如堆起的棉花,轻飘飘的,慢悠悠的;有时它猛烈,雄浑神秘,带有野气;有时不是在飘,不是在走而是在跑,脚步沉重地跑;有时压得很低很低,像有着金属的沉重,带着愤怒和霸气。根据云的变化,有句家乡的谚语提醒我该注意些什么:“云往东一场空,云往西下大雨,云往南水推船,云往北放牛小子往回跑”。凭着这些经验,我和我的牛很少遭罪。 雄姿英发 牛虽是温顺善良的,一旦发怒,那凶狠的另一面十分可怕。有一天我的牛群和邻村的一群牛在东山顶上不期而遇。我的大花牛首先发难,只听它“哞、哞”的几声叫唤,前蹄刨地,扬起股股黄尘,两眼瞪的如同铃铛,头也在不停地晃荡,一会儿朝天,一会儿磕地,显然是亢奋极了。另一群的一头大黑牛也“哞、哞”地叫了几声,以示应战,顷刻两牛冲出阵前,四只大角轰雷掣电似的撞到了一起,忽进忽退,声势浩大,它们倾尽全力,一决高下。我和那放牛老汉上前拉架,根本靠不了边,牛那蛮劲一旦上来,雷劈闪电也不管不顾。几个回合,我的牛因地形不利,眼睁睁地随着一团烟尘掉下沟里去了……我灰溜溜地像撂了魂似地跑回村,急忙告诉了父亲。父亲气得捶胸顿足,举在半空的手又放了下去,我闭着眼睛,做好了挨打的准备。生产队里可有的人高兴坏了,他们分到了牛肉。(那年月吃上点肉是很难的)人们像过年似的。当然我家也分到了应有的那份,可父亲连闻都没闻。那几天牛肉的香味飘了半个村子,可父亲却愁眉苦脸,打不起精神,像丢了儿子似的。他把我像押俘虏那样带到了村支书那里赔罪,并请求赔款。支书大腿一拍,“赔个球哇,算了,管娃屁事”。事情不了了之,可我的牛“官”是当不成了,父亲撤了我的职。我又回到了田里,被强制地列入了壮劳力的行列。 心里憋屈,借来小说解闷,看完了。又用鸡蛋换钱买书,《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烈火金刚》《红旗谱》《红日》等一大摞。晚上全家人都睡了,我遨游在小说里,真是“三更灯火五更鸡”,如痴如醉放不下。父亲见我如此上心,他的脸阴转晴,好象以前那恨铁不成刚的气恼少了许多。吃饭时关心我的话也多了起来,晚上还安顿我早点睡,有时还嘱咐母亲给煮几个鸡蛋,说“娃娃”瘦的,吃不上好东西不行啊。“你咋心疼起儿子来了?”母亲诧异。“看你说的,老子的儿子老子能不心疼嘛,就你心疼啊”。父亲的确疼我,是出在骨子里的,只不过不像母亲那样无微不至,猫猫狗狗的。 一年又一年,天荒地也老。“人之少壮天之晨”。父亲对这一点是有深刻认识的,深怕耽误了我的前程。“咱进不了县中学,到别的地方也行,只要能念书到哪里也一样”。这几乎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看来父亲从没放弃让我读书的机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机会终于来啦。一天傍晚父亲从集上回来,很兴奋地对我说:“娃子,听说有一所林业中学招生,你去考吧,要使出吃奶的劲给老子考上”。“嗯”我答应。 对这种非正规的学校,从本心来说我是不以为然的,但为了父亲那双期盼的眼睛,总得去试试。一试考上了,像有神鬼帮忙似的。去学校报到的那天,父亲背着我的行李,我跟在他的身后。他那长腿大脚走起来像流星赶月似的,那是高兴的,身后好像有个状元郎跟着。我恨也不是,爱也不能,唉!算啦,“莫以山田薄,今春又不耕”。为了满足我那可怜的父亲,还是念吧。 刚念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老师坐不住了,学生坐不住了。“革命大串联”开始。一批批的学生扛着红旗从家乡走过,他们那种“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劲头看似十足。没多久,我们也走,到了省城,又上北京、再南下广州……外面的世界精彩,洋戏匣子、高音喇叭、红墙黄瓦、高楼大厦,人流如潮。我等井底之蛙,算是开了眼界,见了世面。每到一地,我们都是急着上街,游山玩水,免费享受。谁还顾得上看那些大字报和听喇叭呢。 一场大串联的“洗礼”,校长管不了老师,老师管不了学生,谁都是革命者,自由人。没过多久,同学们大多都作鸟兽散,黄粱一梦再现。 第二年开春,“复课闹革命”,有的回到了学校,有的黄鹤一去不复返。名曰“复课”,纯属变相劳动,春天栽树,秋天还是栽树,夏天砍桦杆,冬天上山打柴禾。同学们接累带饿,面有菜色,脚无完履。家乡的大南山我们是走遍了。什么大火尖、二火尖、三火尖、黄儿窊,直至宁武的大石洞、小石门。那里夏天蚊毒如狼,冬天林海雪原。有人看不惯,说“林校的学生都成劳改犯了。”我们听到后气恼又伤心。有几位要好的同学约定:这鬼学校咱不念了,谁也“不学桃李花,乱向春风落”。 因为有个约定,春天过后,夏天又来,父亲见我迟迟不动,问我:“开学了吧?”“早开了。”“那你咋还不走?”“不念了。”“你敢”!父亲瞪起了眼。“你瞪眼也没用,你打死我也不念了”。我回答。父亲见我不可理喻,举起的巴掌又放下,放下又举起,最终拍到了那顶榆木大柜上,震得那些瓶瓶罐罐蹦蹦跳跳地滚到了地上,噼哩啪啦地都碎了。那一巴掌要是拍到我的身上,至少也落个三等残废。“唉,这个灰东西!”一扭头不理我了,只见他的胸脯一鼓一鼓的,气坏了,母亲见父亲生气,又怕父亲真的打我,只好打圆场:“算了,算了,谁叫咱娃不是那个料,人各有命,你逼他也没用”。父亲“哼”地一声出门去了。 作者年时任保德县武装部部长戎装照 我“官”复原职,赶着我的一群牲口,重复着原来的路程。有所不同的是,我好像一下子长大了,再不敢漫不经心,再不能给父亲招灾惹祸。身上还多了一件东西—— 小说。把牲口们赶到一个远离庄稼的地方,他们悠闲地吃草、倒嚼,我看我的闲书,互不打搅。小说里的故事一次次将我醉倒,那里有振奋,有担心,有摩拳擦掌,有咬牙切齿,也有山前岭后、花前月下。正如宋朝皇帝赵恒所说: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他的劝学诗是一幅太平盛世的浪漫,故意隐匿了宋朝的内忧外患。而我见到的书里是一个民族的愤怒、呐喊,是抗争冲锋,是流血牺牲。少剑波、杨子荣、小白鸽、林道静、朱老忠、喜儿和大春……这些英雄们如同一个个鲜活的人,微笑着朝我走来。小说成了我的无言老师,用笑与泪与我对话,与我交流,启迪我、教育我,我时而激动,时而悲愤,因为他们我流过许多泪,也曾笑出了声。小说是我认识社会、认识生活的引路人。 每每日薄西山的时候,我的大黄牛“哞、哞”的几声,提醒我该回家了。我抬头眺望村庄,但见炊烟四起,一缕追着一缕向远处飘去。我赶紧收拢“部队”,浩浩荡荡地向村里奔去,一路上我唱着:“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奋发,斗志昂扬………”“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的彩,一十三省的女儿呀,唯有那个兰花花好………”“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 那不是唱,是喊,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个甚来唱个甚,那是高兴,是自娱自乐,因为我又看了半本书。 夫妻合照 “花落徒绕枝,流水无返期,莫恃少年时,少年能几时”?我如大梦初醒,暗下决心要象小说里的英雄们那样轰轰烈烈地活一回,我的心已向我崇拜的偶像们奔去…… 那年冬天,我决定去当兵,为了给父亲给自己争一口气。父亲知道后又燃起了新的希望。他主动捐弃前嫌,连声称赞:“当兵好,当兵好哇,男儿当自强,人小志气大。”第一次听到了父亲的赞叹,也是第一次和父亲取得一致。通过体检、政审、家访等一系列程序,我拿到了入伍通知书。父亲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爱不释手,喜笑颜开。仿佛那不是一张入伍通知书,而是一张入学录取书。我暗自觉得父亲太看重读书,太痴迷文化了,他盼儿成材简直要到发疯的程度。父亲说:“到了部队更要多学习,多看书,当上几年兵,复员后说不定当个煤矿工人什么的。”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这是第一次和父亲不谋而合,“英雄所见略同。”一只鸡的理想也就是一把粗糠,这是我当时的内心写照。母亲后悔了,哭哭啼啼死活不让我走。嫌父亲心硬,不近人情:“娃娃放牛放的好好的,已经够累了,你咋还叫他当兵……”父亲火了,突然冒出一句:“老子当年要是南下了,说不准已是个区长、县长什么的,娘们就是短见识”。“娃儿你说呢?”父亲朝我挤了挤眼,我明白了父亲的意思,“就是嘛,入伍通知书都拿到了,准不能当逃兵吧”。父亲乐了。我第一次看到他甚至不快乐,也会把仅存的笑容挤给我看。顿时我的胸中涌起了一股莫名的悲凉,一下子懂得了什么叫父爱。 我就这样迫不及待地离开了家,猛然间有一种“溪间岂能留的住,终归大海做波涛”的冲动和自信。当列车一路狂奔,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途中广袤的原野在窗外疾速的闪过,祖国那大好河山将由我们保卫,“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民族的希望……”我心潮澎湃,我壮怀激烈。子夜时分我们到了目的地。锣鼓喧天,鲜红的大幅标语在灯光下醒目可见。营房里的老兵们列队欢迎我们,歌声、口号声响彻天际。那一刻我觉得到了一个新世界,什么都新鲜可爱,什么都让我激动不已,真有一种如鱼得水的感觉,那一夜我睡的特别香。 在军营的三年里,我入党提干,一张张喜报接二连三地发至家里,每次父亲拿到手上时都抖而打颤的异常激动,并要喝上几杯老酒,以示庆祝。他想我时一封封家书千里写叮咛,他盼我时一袋袋闷烟满天数星斗。这是所有军人父母的共同心路。 我是有点出息了,可我的父亲却早早地走了,那是年秋天的一个晚上,父亲无声无息地走了,终年60岁。他在弥留之际握着我的手有气无力地说:“爸虽没文化,可有句话是知道的,‘武将不怕死,文官不爱钱’你可不能有闪失啊!”我咚地双膝跪地,泪如泉涌,哽不能语。这就是一位农民父亲的崇高和遗嘱,我牢牢地记下了。 我到何处去偿还这一笔无法再还的心债?我怎么弥补自己对父亲的内疚。父亲经历沧桑,半生苍凉,父亲指点江山,穷则思变。我只觉得写父亲,太沉重。这不,父亲的影子又在我的眼前…… (本文年8月发表于忻州日报副刊,图片提供:作者) 作者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证 作者年到管涔山里的大沟村看望60年前的小学老师、现已81岁高龄的李景林老人 宗光华,年7月10日出生于山西省神池县大严备乡九仁村。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历任战士、班长、学员。从军三十二年,正团职,上校军衔。在部队退休后,从事文学创作,有五十余篇稿件,发表于省市县级文学刊,并有专著《军人情怀》一书出版。现为神池县作协副主席、山西省散文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现今所创作的第二部《军魂永铸》约30万字,即将面世。 本文来源:《桑梓情怀》第一册第十六篇 本期编辑:肖巍 图、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fz/8467.html
- 上一篇文章: 伊妮莎莉鸵鸟油的神奇功效你不知道它
- 下一篇文章: 夏天必备的小药箱伊妮莎莉shys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