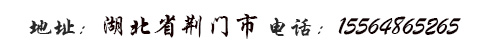95后年轻人独自去手术
|
一个人做手术,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年,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新独居时代报告》预测,到年全国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其中20-~39岁独居青年或将从年的万增加到年的~万人,增长约1~2倍。 生存结构的变化令都市中的年轻人不得不“独立”起来,除了需要处理生活中琐碎繁杂的小事,就连做手术这样的重大变故,他们也选择自己一人面对。 一位99年的女孩儿曾半开玩笑地说:“万一我真的不幸逝世的话该怎么办?要不要留下一封遗书”“真的感受到了人类十级孤独”...在面临生死临界点,以及身体极端情况下,一群城市孤独患者又有怎样的思考,关于人生、未来、拼搏与奋斗,生活又给他们上了怎样的一课? 众面(ID:ZhongMian_ZM)最近也与几位单独做手术的95后年轻人聊了聊,大到关于选择、关于人生,小到关于当下如何“抵御孤独”等看似不同,却贯穿人类一生的课题。看看他们的思考与抉择。 01“独自手术后,想要写一封遗书” 黄思思恢复意识的一瞬间,发现自己身上连着无数种仪器,而自己动弹不得——左右手都打着吊瓶,背部插着运输阵痛剂的管道,下体插着尿管,目光所及之处,还有心率监测仪和测量血压的仪器。 几小时前,妇科医生为她从子宫中取出了一个长约12厘米的肿瘤,并在她的身上留下了一个11厘米长的刀口。 这是一场全麻手术,黄思思为数不多关于手术过程的记忆,就是手术前医生领着她从六楼的病房下到三楼的麻醉室,通往麻醉室的通道大门一层层地打开,她能够明显地感受到医院走廊所没有的寒气。 她这样形容麻醉室:“它是一个非常阴凉的地方,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模一样。” 房间中心放着一张小床,病床四周则围绕着移动推车和各式各样的器材:剪刀、绷带,还有一些她叫不上名来的医疗器械。她褪去连体手术服,爬上床,再弓起背部,以便医生进行硬膜外麻醉——这是她从出生到现在打的最疼的一次针,她能感受到医生拿着针在往她骨骼里钻。 黄思思说:“我感觉自己有点可怜,像任人摆布的羔羊。”之后,医生又为她戴上了一个释放麻醉药物的呼吸面罩,她清楚的记得这种麻醉药效很强,因为在戴上面罩后的几秒钟,她就迅速失去了意识。 ▲图:黄思思躺在病床上看到的夕阳 时间回到一年前。 年10月,黄思思发现自己一连来了两周的例假,一开始她没当回事儿,但一个月后,同样的事情又再次重演。通常而言,女性的经期在3~7天之间,14天已经算是异常信号。 直至今年2月,她发现肚皮有些鼓,同时摁压又能感受到硬块,她隐隐约约的觉得:大概是子宫出了问题。不巧的是,在日本留学的她恰好遇到留卡(允许外国人中长期停留在日的证件)过期、无法使用保险,因搬家扭伤腰部只得静躺休养等一系列问题,看病的日期只好一再拖延。 根据日本的医疗制度,患者需要先去诊所进行病情诊断,如果较为严重,医院。如果没有诊所的介绍信,医院将不予接诊。 今年5月,黄思思一连来了20多天的例假,失血量远超正常经期,造成中度贫血,这一次,她总算敲开了妇科诊所的大门。黄思思还记得那家诊所的医生给她随意扫了个B超,就告诉她:“你的子宫肌瘤很明显。”这是在女性身上常见的一种良性肿瘤,唯有手术才能摘除。 她和家人讨论了很长时间,究竟是回国做手术,还是留在日本做。回国,机票、手术费等支出相加至少需要一万元,而留在日本,则可以享受留学生等无收入群体特享的“限定费用”,即不论住院期间花了多少钱,她只需要支付元人民币即可出院。 另一方面,她的父母由于工作原因,无法申请长假飞往日本,综合考量后,黄思思决定一个人接受手术。 为了避免手术时碰到肠道,保持清洁,她需要在手术的前一天吃下泻药,并在手术当天进行一次灌肠。术后,她花了10天左右的时间才勉强恢复到正常状态,在恢复初期,她每天只能弯着身子,以龟速驱动身体前进。 医院住了整整八天,虽然偶尔会在深夜陷入伤感情绪,甚至想过要不要留下一封遗书,但每当白天来临,她就又恢复了积极乐观的心态,因为某种程度上,经历过手术后,她发现“很多东西都没有想象中这么可怕”。 02经历裁员后,一个人做了个手术 年9月,马楚岚被查出左手食指长有一个小小的腱鞘囊肿,导致食指有一处鼓包,需要手术。同时期,她所在的互联网教育公司正在面临大规模裁员,马楚岚所属的事业部几乎全员失业,她也并不例外。 收到裁员消息的马楚岚第一反应是:是不是得赶紧找个时间把手术给做了?不然走不了医保了。就这么想着,年10月,她迅速地医院的骨科病房。 但直到办理完住院手续后,马楚岚才发现身上只有两样东西:一些换洗的衣物和一根手机充电线。 住院部的护士告诉她:“你去楼底下的小卖部买个刮毛刀,把腋毛给刮了。”这一步是为了便于手术时在腋下扎麻醉针,医院的小卖部只收现金,而准备不足的马楚岚不得不到处跟病友借钱。虽然一开始显得有些窘迫,但跟病友熟到一定程度后,她开始蹭病友的洗发水和沐浴露,连同房的大姐也会分她几个水果。 手术当天是工作日,她不想麻烦父母,于是喊了一名同公司跟她一起被裁的朋友过来签字。朋友给她带了些牛奶和水果以示慰问,签完字后便离开了。 那一天,医生拿着一个大碘伏球,从脖子处开始仔仔细细地给马楚岚整条左臂消毒。她说:“我其实能看见我那胳膊就跟腌猪蹄似的,黄黄的。” ▲图:马楚岚的病房 为了手术空腹一晚的她一方面感觉自己饿得慌,另一方面,对手术的担忧又盖过了生理上的饥饿。虽然脸上盖着一层手术洞巾,看不清医生的具体动作,但做了局部麻醉的她能够明显感受到自己的皮肤被刀划开,而她的身体发虚,背后出汗,心脏也跳得飞快。 手术不到半个小时便结束了,待完全清醒后,马楚岚试着用右手碰了一下左臂,发现后者异常烫,且没有任何知觉。其后的凌晨一点,麻醉剂失去效力,马楚岚被疼醒。按六小时一片止疼片的频率,她连着吃了四五片,吃到最后胃里翻江倒海,还有一种隐隐想要作呕的感觉。 想象中的小手术带来的疼痛远超想象,她躺在床上,暗暗后悔做手术的这个决定。“如果从病房走出去,谁要跟我说这个手术很小,一点儿也不疼,我肯定会怼他们。”而马楚岚在住院期间唯一一次哭,是实习护士一不小心把她的血管扎穿的时候。她已经忘记当时是在打针还是抽血,只记得护士一针下去,因为瞬间生理上的剧烈疼痛,她的眼泪“唰”的一下就流了下来。之后的将近一个月,她的小臂有很大一片都是青黄的。 没有家人和朋友陪护的马楚岚跟同房的病友建立了很深的“革命感情”,他们互换了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wuwangwoa.com/wwwzp/11626.html
- 上一篇文章: 独家好书罪全书1,天命所至,从岌岌无
- 下一篇文章: 划重点推荐的年度好书名门暖婚,章章让